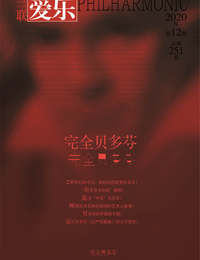贝多芬在场:汉斯•岑德《关于33变奏的33变奏》
作者:爱乐
2020-12-23·阅读时长6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3073个字,产生1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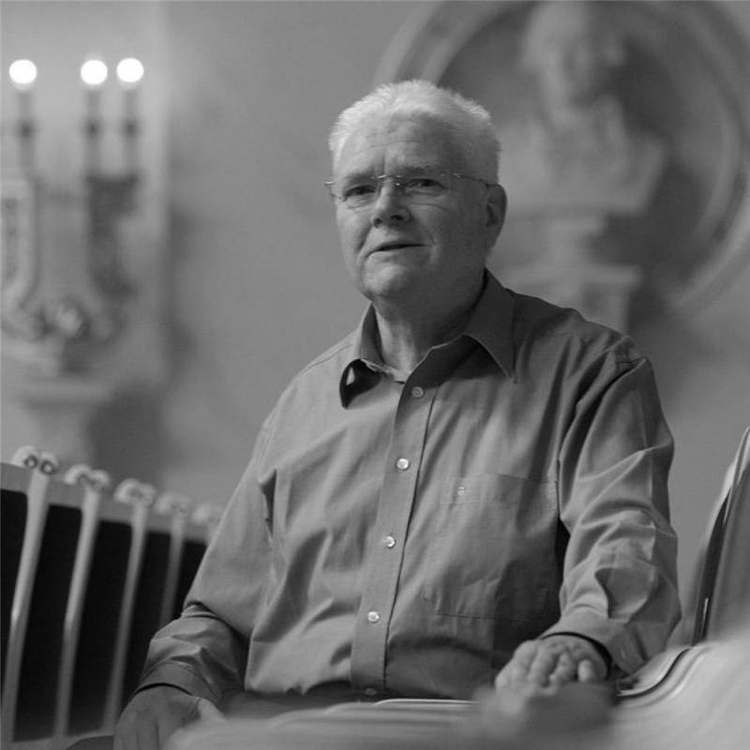
文/孙冰洁
在迪亚贝利圆舞曲主题的33首变奏曲中,
贝多芬总结和预示了从亨德尔到我们时代的音乐发展,
又一次扯下了使我们看不见未来的幕布。
——埃德温•菲舍尔
1823年6月16日的《维也纳日报》,迪亚贝利写道:“我们在此向全世界呈现独一无二、足以和不朽的经典之作并列的伟大而重要的变奏曲,只有贝多芬这位现今最伟大的真正艺术家,只有贝多芬,没有其他人,能创作出如此的作品。最有创意的结构和意念、最大胆的音乐语言以及和声皆呈现其中,运用了每一种以扎实技巧为本的钢琴效果,他的作品比别人的更有趣,原因是我们这位大师独异于当代人,能够运用这种特色从一个主题引导出作品。我们很荣幸能借此机会推出此部作品,并且费尽心思使印刷融合优雅和精确。”
这部作品是《“迪亚贝利”变奏曲》,但贝多芬最初是拒绝这个委约的。早在1819年,维也纳的作曲家兼出版商安东•迪亚贝利与皮埃特罗•卡皮打算成立一个新的出版公司以满足维也纳人对音乐的需求。他们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出版计划。由迪亚贝利自作一首16小节的圆舞曲作为变奏曲的主题,以“本土艺术家协会”的名义,委托维也纳和奥地利的51位作曲家各作一首变奏曲,然后编成一本变奏曲集,按作曲家的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出版。
当时受邀的作曲家有胡梅尔、车尔尼以及11岁的李斯特等等。贝多芬也在受邀名单中,但他厌恶集体创作,也不喜欢迪亚贝利主题,甚至称其为“臭皮匠的补丁”。后来通过申德勒说情,贝多芬才接受这个计划,并许诺7个变奏。但在1819年动笔之后,中间却中断了两年多,直到1822年末才又重新提笔。整个创作过程是不连贯的,这其实完全不符合贝多芬的作曲习惯。
在这中断的期间,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创作《庄严弥撒曲》、晚期三首钢琴奏鸣曲(Op.109、110、111)等,这对他后阶段创作《“迪亚贝利”变奏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最终创作出来的不仅有7段变奏,而是增加到了33段变奏。由于篇幅过大,因此在出版时单独成册。贝多芬不仅改变了迪亚贝利的华尔兹,而且改变了变奏曲的整个形式。正如阿多诺所说,他炸毁了它们,只留下了碎片。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贝多芬把碎片重新拼成全新的形式,在单一的线性历史层面上是不足以理解他的变奏的。贝多芬的作品已经不再是封闭式的形式了,那种线性的时间变成了一种类似碎片的、空间化的时间。在这种时空中,历史可作为一种空间。贝多芬是第一个有意识地作为历史存在去体验和反思的音乐家。
虽然这部作品现在被推崇备至,但对它的定位是有争议的。大部分学者认为这部作品本质上是喜剧式的,是贝多芬对迪亚贝利主题以及对风靡一时的维也纳圆舞曲的文化批判。比如亚伯拉罕在《贝多芬的平庸和讽刺》一文中指出,由于主题具有陈腐性,因此比较适合“滑稽性模仿”(parody)。
贝多芬在变奏中引用其他人的主题,比如变奏22是对莫扎特歌剧的戏仿,变奏23则针对克拉默的钢琴练习曲语汇。此外,他也对主题本身进行戏仿,比如变奏21开头对原主题重复和弦的怪诞夸张。查尔斯•罗森说:“变奏13,迪亚贝利开始几个小节静态的和声在节奏变奏的和弦之后,消失在休止的寂静之中。”变奏曲的幽默感恰是通过对休止这种富于表现力的运用来体现的,而这种幽默性也正是贝多芬晚期作品伟大的艺术整体中一个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在后面的变奏中,贝多芬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主题,而是几乎脱离了主题。这些变形不仅是一种性格变奏,并且是基本理念的分裂。人们可以把这首作品视为喜剧式的,但也可以把它看作悖论式的。在不断进步的追求中,对回顾的倾向令它有种悲剧纹理。这种多义性,是现代音乐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在晚期贝多芬那里已经可以找到了。
它是对某种缺失的唤起,
一次又一次被合奏的疏离声音打断。
如果你愿意,原物会重生。
而这种中断或许是所有乌托邦式的诠释目标:
“过去”作为一种“未来”被带入“现在”。
——汉斯•岑德
文章作者


爱乐
发表文章834篇 获得1个推荐 粉丝18387人
三联书店《爱乐》杂志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