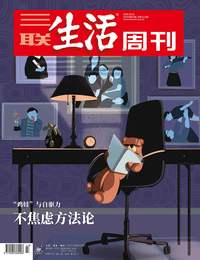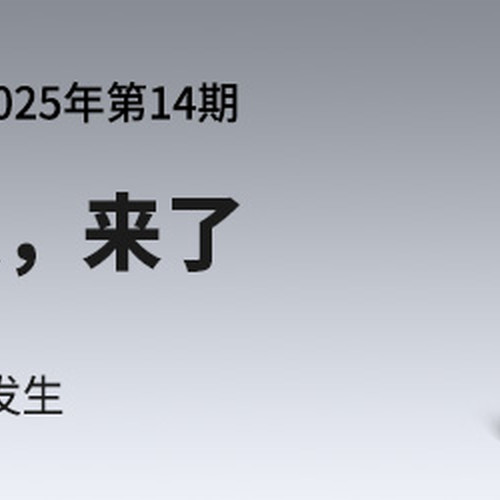我在安宁疗护病房见证的死亡
作者:吴琪
2020-10-21·阅读时长15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7543个字,产生14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刘寅在与病人和家属聊天
口述/刘寅 采写/吴琪 摄影/黄宇
患者何时不再需要积极治疗?
我曾经是北京一家二级医院(后晋级为三级医院)的肿瘤科负责人。医院在北五环外,我们的病人既有北京本地人,也有来京务工人员,还有这些年通过努力在北京安了家的一些人,他们的父母病了后被接到北京治疗。二级医院很难获得首诊的肿瘤病人,到我们医院治疗的,一般都是之前辗转过好几家三级医院的中晚期癌症患者。我能深刻地感受到他们的疲惫和纠结,比如癌痛、经济压力、离世前的悲伤,很多病人在躯体和精神上忍受着非常大的痛苦。
十几年前接触到姑息治疗理念时,我非常感兴趣,在医术之外,我对病人的处境特别能够产生共鸣。当时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的刘端祺主任作为北京抗癌协会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积极推广姑息治疗的理念,得到学会里同仁们的积极响应,我也受到了这些理念的感染,开始了对临终关怀的深入了解和实践。2012年我所在的二级医院成为了卫生部首批67家“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这让我对通过控制癌痛让病人感到舒适,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
退休后,我到了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在肿瘤科建立了安宁疗护病房。目前我们做安宁疗护的对象基本是肿瘤病人,因为晚期肿瘤病人的生存期相对容易评估一些。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一般都与肿瘤科在一起。我们的安宁疗护病区有静修室,有病人画的画儿,有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温暖的话语。接触的病人多了,我发现安宁疗护工作与一个国家的死亡观念、历史文化、患者个人经历等密不可分,有着浓厚的本土特色。一个在医学上“没有治疗价值”的病人,还要不要用抗生素?要不要输血?这些涉及医疗原则、伦理,更涉及病人和家属的诉求,需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而不能把安宁疗护的理念和原则绝对化。

安宁疗护工作是希望陪伴病人走好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从定义上来说,通过医学治疗无法解决这个病人的疾病问题了,才进入姑息对症治疗。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是非常忌讳谈论死亡的,一个病人选择什么态度面对治疗,很多时候没有经过与家人、与医生充分有效的沟通,病人因为对疾病了解的局限性,对治疗方案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们最后的决定不成熟。什么样的病人应该进入姑息治疗阶段,需要面对每个具体的病人来做判断。从生存期的角度看,一般是在生命的最后3~6个月。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病房来了一个患肺癌的老人。老人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学教授,快80岁了,一儿一女分别在国外和北京工作,我叫他张老师。初诊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小细胞肺癌(广泛期)、上腔静脉压迫(颜面及四肢水肿)、两侧胸腔积液、肝转移、骨转移,整个人憋喘很严重。我查房时,张老师非常不情愿地在吃之前医生给他开的依托泊苷胶囊(VP16),他坚决拒绝系统治疗。他为什么不接受治疗?我与病人和家属聊下来,获得这样几个信息:第一,张老师的夫人死于食管癌。夫人做了放疗和化疗,受了好多的罪。等到张老师自己得了癌症,他想起化疗就有心理阴影。他的说法是:“让我早点结束,别让我受罪就行。”第二,张老师查出癌症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他觉得自己不久就要离世了,对自己病情的判断非常悲观。
小细胞肺癌的初次化疗效果一般会非常好,在我看来,张老师当时放弃治疗太可惜了。我第一次动员他时说:“我们给你把胸水(胸腔积液)放一放,胸腔里打点顺铂(一种含铂的抗癌药物),行不行?”他不同意。
过了一个星期,他吃VP16胶囊确实没什么起色,我又跟他沟通。“你这个小细胞肺癌现在处于第一次治疗阶段,不治有点可惜。你喘憋这么重也不舒服,我以改善症状为目的来给你治,咱不以治疗肿瘤为目的,你说好不好?”接着我又说,“张老师,我们用药的目的呢,主要是让你的身体感觉舒服。而且你看2020年的春天,这个世界太热闹了,咱们争取一起看个完整的春天,好不好?”
文章作者


吴琪
发表文章49篇 获得35个推荐 粉丝1615人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