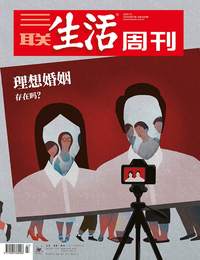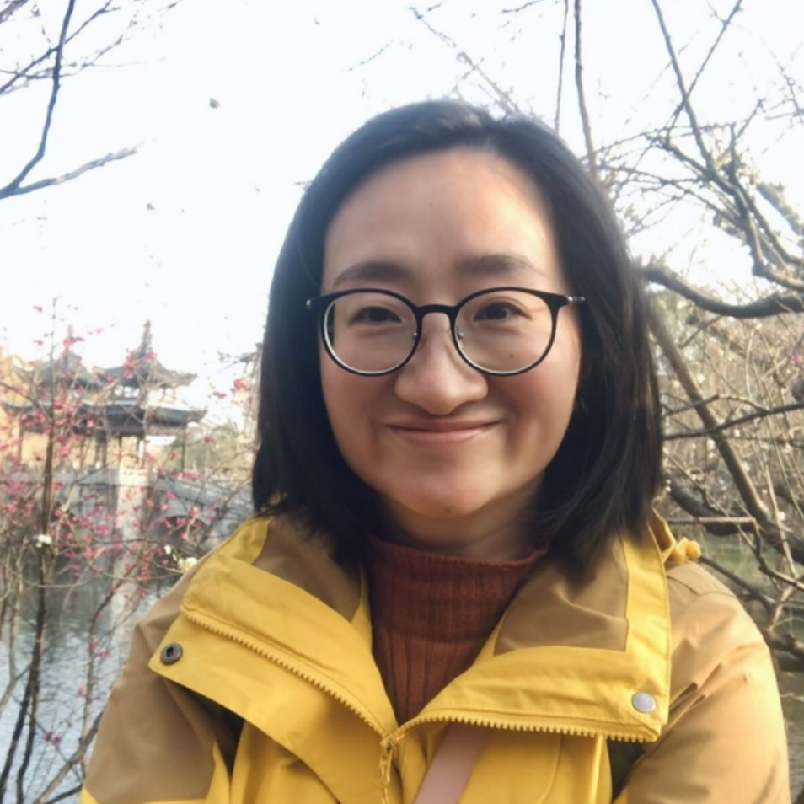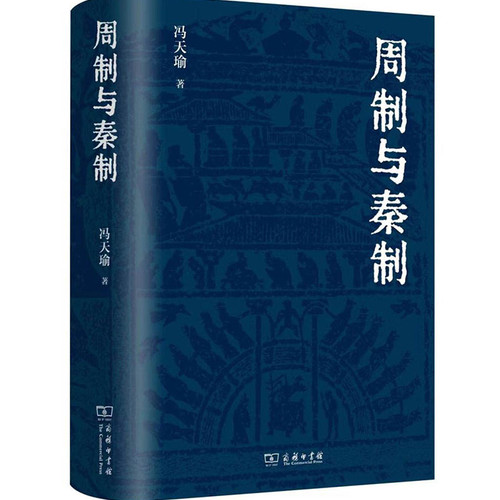官与民的共谋
作者:维舟
2020-07-01·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需付费阅读
文章共计2493个字,产生19条评论
如您已购买,请登录
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
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历来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一种强调它是“大政府”,政府无所不管;另一种却认定它是“小政府”,仅用相对而言很小的一批官僚就有效运作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所谓“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可以表明:生活在基层社区的普通人在现实中很少需要和国家打交道。
现在,加拿大汉学家宋怡明同时推翻了上述两种设想,呈现出一幅远为复杂深入的景象:一方面,即便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普通人,其实也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应对无所不在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只有服从或反抗两种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可以利用正式制度中的种种矛盾和缝隙,将之转化为自己生活中的有利因素,而这正意味着国家无法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明代出现的“阳奉阴违”一词,传神地体现出这种双向博弈。
这种特殊的制度史在意的并非文献上记载的成文法条,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在此他选取的是明朝的特定群体:军户,也就是按规定必须世代服兵役的那些家庭。以往的研究大多注意到,军户制度越到后来越难以为继,因为随着军户人口增长、社会变化,后世未必愿意当兵,也不见得适合当兵,到后来兵源素质下降、逃兵屡禁不止,又或出钱找人替补,引发层出不穷的问题。无疑,这也常被视为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但这本《被统治的艺术》却通过对家谱等地方文献的视角揭开了另一面:这些老百姓在苦于应对正式制度的同时,也在“紧紧抓住国家提供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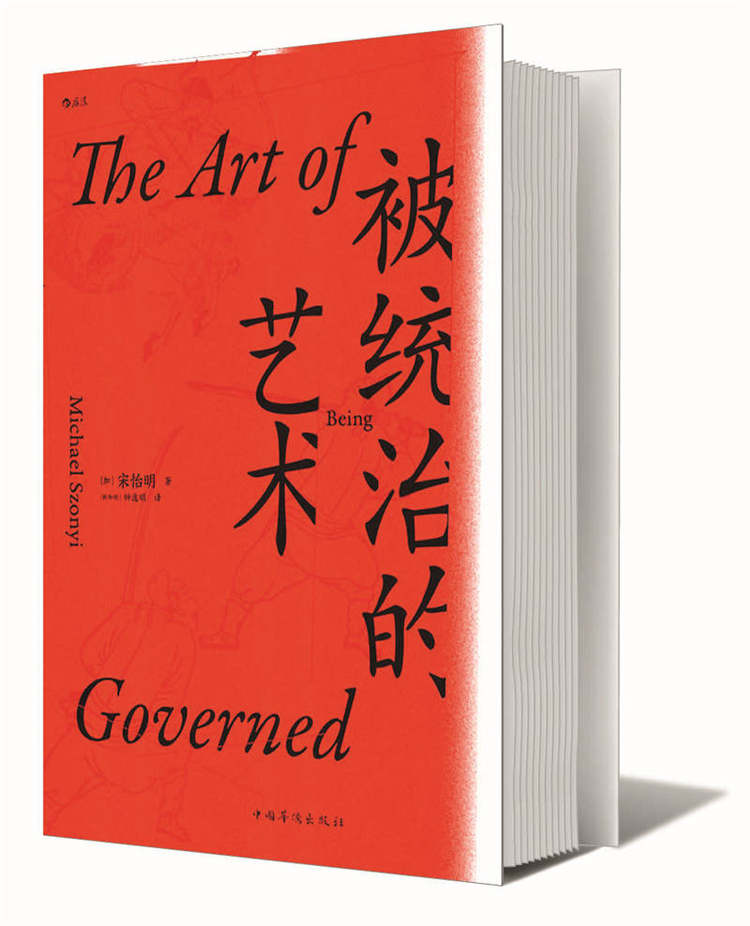
《被统治的艺术》
因此,“被统治的艺术”乍看谈的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其实却着眼于他们的主动性。在这样的庶民政治的视角下,普通人也是历史事件的主体,他们不仅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历史,也的确通过深思熟虑的利弊权衡,评估着各种不同选择的代价,尽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确,国家特定的义务必须履行,但他们还是可以有条件、有选择地履行。这里的办法有好多种:首先是“集中”,即由一人承担起整个家族的服役重任,这个人甚至可以是雇来代役的;其次是“轮替”,也就是家族内部轮流出人来承担。
不难看出,在这些百姓眼里,服役与其说是一项光荣的使命、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项无偿的义务。鲍大可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中曾说,1949年前藏区很多人把政府开办学校、强制义务教育也看作跟征兵一样的徭役,因而出现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钱人家的父母出钱雇农奴子女代替自己的孩子去上学。
但明代百姓并不只是被动地应付,他们很快发现,军户身份也自有其好处:正因为军户已经承担兵役,因而就免除了像民户那样“交皇粮”的义务,否则就构成双重赋税了,因而整个家族只要有人去服兵役,就别无负担,也因此不愿脱离军户,这种徭役豁免权到后来甚至越来越有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利用军户的好处,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触到航海技术和船只,甚至在非法贸易中获利,特别是负责控制、取缔非法海上贸易的人就是他们自己人,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靠近国家机关。
文章作者


维舟
发表文章33篇 获得2个推荐 粉丝419人
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
收录专栏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