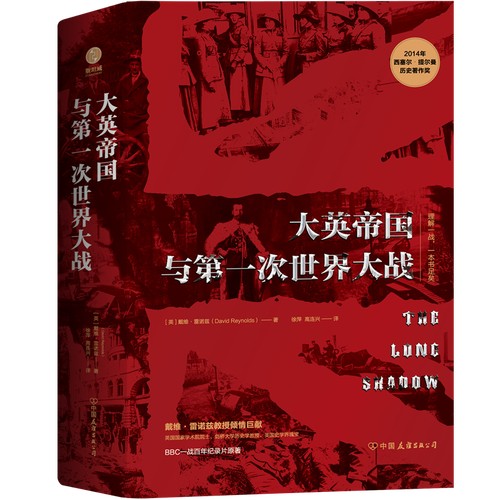《重返查令街84号》|遇见一本书
作者:新经典文化
2019-05-30·阅读时长4分钟
本文摘自《重返查令十字街84号》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五
闹钟在八点钟准时响起,我下床走到窗边,急于知道是否还在下雨。打开窗帘——啊,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我就永远忘不了这一刻。街对面,一排整整齐齐的狭窄砖屋俯伏在那里,仰视着我,门前都有清一色的白阶梯。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住宅,一看见它们,我就知道我是铁定无疑身在伦敦了。我一阵眩晕。我遏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要奔上街去。我抓起衣服,冲进淋浴室,与我所见到的最要命的淋浴器打了一场败仗。
淋浴室是一个四英尺的小隔间,只有一个水龙头,它是不可调节方向的,对准了后面的角落。旋开龙头,水是冷的,继续旋动,等到水温够热可洗淋浴时,水量已被你开到最大一挡,倾泻而下,这时你爬进去蹲在后面的角落里,接受水的洗礼。一旦失手让肥皂落下,我那价值十五美元的发型便立刻付诸东流,因为水柱把我的淋浴帽从头上打落。关上龙头,谢天谢地,我跨了出去,却一脚踏进四英尺宽的水塘。我花了足足十五分钟,用浴垫和两条浴巾去擦拭地面,让它们吸足水,再把它们拧干,吸水、拧干,吸水、拧干。幸好我关上了洗手间的门,否则我的行李箱就要顺流而去了。
早餐之后,我冒雨出去观赏那些住宅。这座酒店在大罗素街和布鲁姆斯伯里街的交角上。它面对作为商业街的大罗素街,我从窗口看到的住宅就坐落在布鲁姆斯伯里街上。
我沿着街道慢慢踱步,打量着对面的屋子。来到拐角,走进一个隐秘的小公园,名叫贝德福德广场。它的三面都有一排排整齐、狭窄的砖屋,这些住宅更加漂亮,保养得非常完善。我在公园长椅上坐下,看着这些屋子。我的心在震荡,我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快乐过。
我一生都在期盼来伦敦看看,过去我常去看英国电影,仅是为了领略这样的屋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我注视着银幕,我如此热切地想要走进那些街道,这种如饥似渴的冲动在噬咬着我。有时晚上我在家里,读到一段黑兹利特或利·亨特对伦敦所做的恣意描写,我会突然扔下书,被一阵渴望的波澜吞没,好似坠落在乡愁的深井里。我想看伦敦,犹如老人在临死前想要看自己的家。我曾经对自己说,对一个生来就和莎士比亚的语言结缘的作家和书迷,这是很自然的感觉。但是,此刻坐在贝德福德广场的长椅上,我想到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玛丽·贝利。
我有非常复杂的血统,其中包含一个名叫贝利的英国贵格会教徒家庭的血统,那个家庭有个女儿叫玛丽·贝利,一八○七年生于费城,她是我儿时唯一感兴趣的祖先。她留下一件绣花样品,我曾常常凝视它,希望它能告诉我她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想知道。
坐在贝德福德广场,我提醒自己,玛丽·贝利生于费城,死于弗吉尼亚,从来没有看过伦敦。但是那个名字一直留在我的脑中,也许她是一个同名的人。也许那是她的祖母或是想要再回家的曾祖母。坐在那里,我只知道,某个早就逝世的玛丽·贝利终于找到一个子孙替她回家了。
我返回旅馆,把自己重新打扮了一番,这样可以给多伊奇的团队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我刷了刷我的深蓝短上衣(这在老家美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花了足足半个小时,将我那条红白蓝三色的新围巾打成阔领带的式样,如此,我看上去会像个英国人。然后我下楼去大厅,身子笔直地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我不敢动,害怕弄乱我的装束,直到一个年轻的秘书闯入,陪我沿着大罗素街直上三个门面到了多伊奇公司。
我和卡门见面了——她非常敏锐、精干,模样惹人注目——接受《标准晚报》一位名叫瓦莱丽·詹金斯的记者采访,她很年轻、富有生气。采访结束后,我们三人加上一名摄影师挤进一辆出租车,卡门对驾驶员说:“查令十字街84号。”
我感到有些紧张,我知道此刻是在去那个地址的路上。我从查令十字街84号买了二十年的书,结交了那里一些从未见过面的朋友。我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购买的大多数书也许在纽约也能淘到,多年来我的朋友建议我“去奥马利书店试试”“去多贝与派因书店试试”,我从来没有另辟蹊径,我想和伦敦保持牢固的联系,我无愧于此,我成功地坚持下来了。
查令十字街是一条狭窄的充塞着下等酒吧的街道,交通阻滞不畅。一家家旧书店沿着街道排列,在门前敞开的摊位上堆满了旧书和旧杂志,四下里有人漫不经心地在蒙蒙细雨中浏览旧书。
我们在查令十字街84号下车,多伊奇公司已经用书把空着的橱窗塞满。橱窗后面的店堂非常幽暗,里面荡然无物。卡门到隔壁的普尔书店拿来钥匙,让我们进入这家昔日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
两个大房间已经被清空,一目了然。甚至沉重的橡木架子也被扯离墙壁,翻倒在地板上,布满了灰尘,成了无人过问的弃儿。我上了楼,进入另一层空旷阴森的房间。贴在窗上用来拼成“马克斯与科恩书店”的字母,从玻璃上被撕下来,有一些躺在窗台上,它们的白色油漆碎裂,剥落。
我开始走回楼下,心中想着一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和他通了这么多年的信。楼梯下到一半,我把手放在橡木扶手上,默默对他说:“怎么样,弗兰克?我终于到了这里。”
我们走到外面——我站在那里,任他们摆布拍照,那副顺从的样子就像我惯于此道。我如此急切,只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给谁添任何麻烦。
当我返回酒店,服务台上有一封信。来自帕特·巴克利,那位老伊顿人,说是琼·埃利去信谈到我。
没有称呼,单刀直入:
琼·埃利来信说你第一次到访这里。星期日七点三十分,你能赏光来用个晚餐吗?——我们会开车四处转转,领略一下老伦敦的风采。
星期六或星期日早上九点三十分之前给我电话。
草就
P. B.

文章作者


新经典文化
发表文章25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737人
优质内容的发现者 创造者 守护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