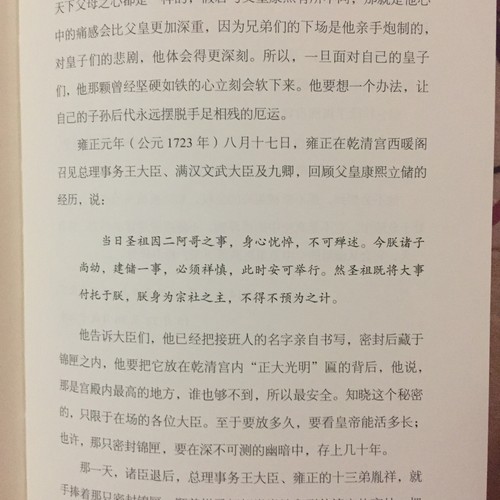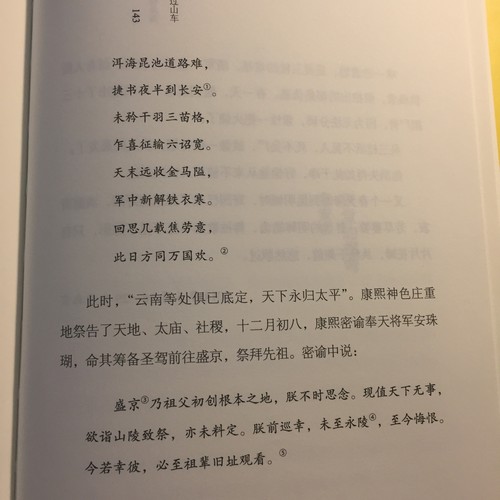#21日打卡#《故宫的隐秘角落》(6)
作者:走四儿
2018-07-06·阅读时长3分钟
5、文渊阁-文人的骨头(1)
祝勇说:在故宫上班,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守在寿安宫里,读《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四百六十万页,当年在紫禁城,需要一整座宫殿来存放,这座宫殿,就是文渊阁。
文渊阁在故宫的东侧,坐落在文华殿后院,现已书去楼空。国民政府在仓狂狼狈地撤退时,没有忘记带上在三万多册图书,而今,这些漂洋过海的书安然无恙地躺在台北故宫的库房中。而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却像走丢了孩子的母亲一样孤独悲凉地一直守候在那里。
大明灭亡,文人才子誓死效忠旧朝,康熙十七年,帝下诏开“博学鸿词”科,张“招贤纳士”之网,却受到李颙、顾炎武、傅山、黄宗羲等文人的以死相拒。然而,康熙深知,士大夫的骨头再硬,也经不住时间的磨损,新朝的盛世气象迟早会让他们坚硬的身段变软。在康熙帝多次诚恳相邀之下,黄宗羲的儿子和弟子、顾炎武的外甥、傅山都进了“明史馆”,参与《明史》的编修,李颙不仅派了儿子进京,还送了两部自己的著作给康熙帝,以示歉疚,甚至连明室后裔朱彝尊都入值南书房,而躲进山村的张岱也终于出山,参与编修《明史纪事本末》,历史再次证明再硬的骨头也经不住皇权的磨蚀,即使自己坚守,也不会断送子孙前程,“我为我国而亡,子为我家成”。
而当新的王朝走到乾隆手中时,一百多年的时光早已将旧朝的恩怨淡化在漫长的岁月中,而经历康熙雍正两朝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时代赋予了乾隆成为“千古一帝”的机会,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当即批准,这一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
在那个文字狱大兴的年代里,入馆编书成为一种高危职业,征书、编书、抄书者稍有不慎就会被罚俸、革职甚至处死。而满汉之间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学术不公,新朝前朝之间的阶级仇民族恨让众多文人避而远之。虽如此,在纪晓岚的举荐下,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等人还是以学术为信念,带领2840多人,埋首四库馆,眷写油灯下,历经十年,于康熙四十六年,完成了第一部《四库全书》,再经六年,完成全部七部,装裱成书。
乾隆帝下江南,不仅见识了江南烟雨,也濡染了江南文风,四十一年,故宫建立起一座与江南私家藏书楼“风雨天一阁”一模一样的图书馆—文渊阁。文渊阁的金丝楠木书架上整齐码放着一只只书盒,每一册书首页均钤“文渊阁宝”印,末页钤“乾隆预览之宝”玺,后再建承德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沈阳)文溯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天宁寺文汇阁以及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文澜阁六座藏书楼,与故宫的文渊阁一道,将七部《四库全书》分存七楼,其中镇江、扬州和杭州的南三阁对民间人士开放,自此有了乾嘉学派,读书笔记在清代走向成熟。
然而岁月风雨飘摇,战乱频仍,人尚无安巢之地,何况书乎,朱棣下令编撰的《永乐大典》便毁于明末战乱,《四库》也难逃岁月的撕扯,首先是镇江的文宗阁,鸦片战争先遭英军洗劫,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镇江,一把火烧毁金山寺的同时,文宗阁内那些精美的书卷,也化作青烟缕缕,然后太平军挥师北上,攻占扬州,文汇阁自此化作一片灰土,咸丰十年,李秀成入杭州,文澜阁劫数难逃,自此,只存在了七十多年的南三阁消失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成为文人心中恍惚存在过的一个梦幻。
1860年,那两个被雨果成为强盗的英法流氓,闯入圆明园,贪婪无耻地大肆洗劫,与那些古董玉器相比,文源阁书架上的那些凝聚着近三千人十六年心血的《四库全书》如垃圾般被他们的一双双脏手撕扯着,一双双臭脚踩踏着,最后,这些丧心病狂的流氓们在所有的建筑上摆满了柴堆,“那座皇家藏书阁,贮满了乾隆皇帝,和一代代文人的心血,在惊天动地的抢劫中,孤独地站立着。黑色的瓦顶,远处燃烧的火光为他镀上了一层凄迷的光,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关于文源阁最后的记录”。一场泯灭人性的大火之后,昆明湖湖底沉淀了厚厚一层灰烬,湖中的硅藻,从此灭绝。
藏书楼毁了,深埋于汉文人心中的书情却没有消失,一生苦读诗书、力求“内圣外王”的曾国藩,派自己的朋友、目录学家莫友芝前往镇江、扬州,四处查访从文宗阁和文汇阁里散落的书册,莫友芝一无所获,最终伤感地离开。他在给曾国藩的信里无奈地写下八个字“听付贼炬,惟有浩叹。”
文章作者

走四儿
发表文章6篇 获得6个推荐 粉丝10人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