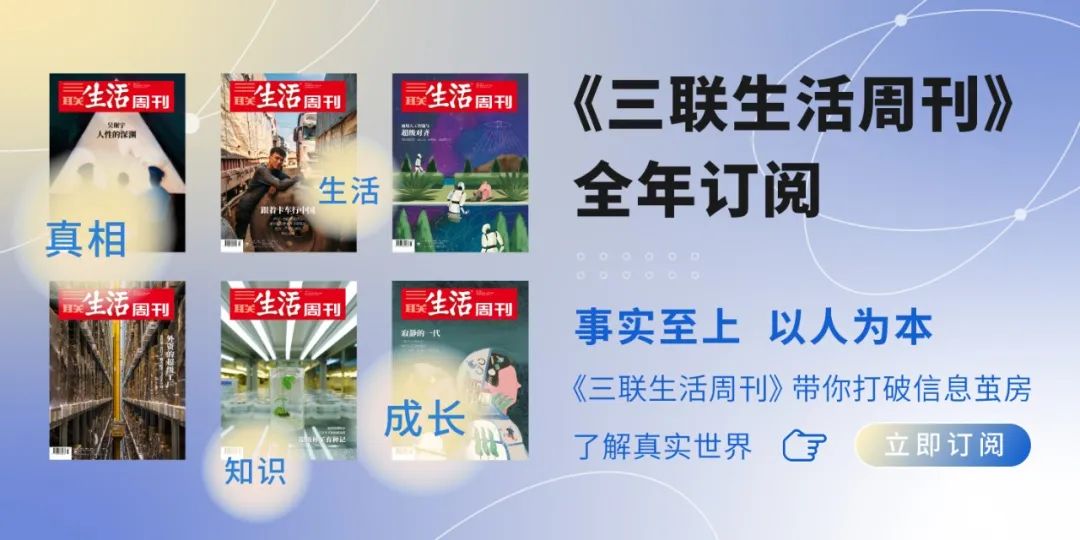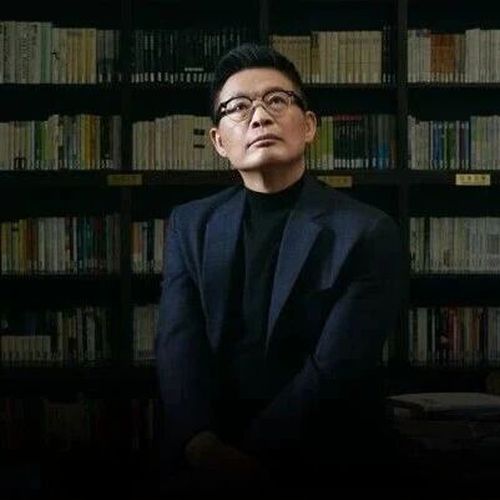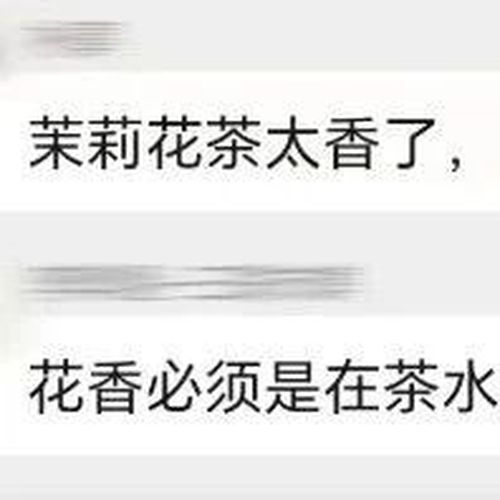千万中产家长,为什么都在“鸡”娃学乐器?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9-21·阅读时长25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全国的交响乐团当中,不少乐团都有天津茱莉亚学院毕业生的身影。天津茱莉亚学院是美国茱莉亚学院在中国设立的首家海外分校,2020年秋季正式开学。与美国不同的是,学历教育方面,天津茱莉亚学院目前只提供硕士学位,并且聚焦合奏精神和技能的培养。国内从附小、附中到音乐学院的教育体系更偏重独奏型人才的养成,这就让天津茱莉亚学院的毕业生格外受到交响乐团的青睐。
为了了解天津茱莉亚学院选择发展合奏型专业的原因,本刊专访到了天津茱莉亚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艺术总监何为。何为出生在四川成都,7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85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附中,1991年获得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来到天津茱莉亚学院之前,他是美国旧金山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及弦乐系主任。从事教育的工作之外,他还是一位活跃的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何为分析了中西方在音乐教育上理念的差异,解释了合奏训练为何会缺失。相比国外,疫情之后的中国古典音乐演出市场依然活跃,交响乐团近年来数量增多便是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合奏型人才显得更为可贵。
主笔|丘濂
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不止一位音乐家都做过“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这样的论断。他们通常会谈到一个现象:古典音乐现场的观众,欧美国家大多数是老年人,中国则大多数是年轻人。结合美国茱莉亚学院来到天津进行合作办学,你是否能首先谈谈怎样看待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潜力?
何为:中国人很注重孩子在音乐素养上的培养,这来自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它的意思是用诗歌来激发情感志向,用礼制规范来立身行事,用音乐来完善人格境界。可见音乐对孩子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兴趣爱好,它是修身养性的必须,这一点是和西方人思维不一样的。据我了解,一个中国家庭如果面临音乐、体育和美术三方面的教育选择,绝大多数家庭还是会首选音乐方面,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讲,其实音乐方面的特长很难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加分,这会让一些孩子成长到某个阶段放弃对音乐的学习。但在孩子的启蒙阶段,家长还是会倾向把音乐作为素质教育的选项。
因此中国和西方的古典音乐受众是不一样的。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概有3600万的“琴童”,琴童和琴童家长是聆听古典音乐的主要人群之一。而在国外,一个城市的音乐厅和它的交响乐团会有一批忠实的乐迷,他们来听音乐会和自己孩子学不学乐器没有关系。他们会在一个音乐季发布的时候,就选择好想要参加的场次来买好全年的套票。他们无所谓演出的是不是一定是名家名团,听音乐会就是一种日常习惯。这样的乐迷在国内还是个较小的群体,但也在不断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专业设置是和纽约的茱莉亚学院不一样的。这同样是基于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特殊情况吗?
何为:天津茱莉亚学院在办学之前曾经做过市场调研。中国古典音乐市场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各个城市的大剧院、音乐厅有一段蓬勃建设的时期。就拿天津来说,2012年这里落成了天津大剧院,2017年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也投入运营,这些地方都有超过1000个座位的歌剧厅、音乐厅。同时,各个城市也在陆续成立交响乐团。疫情之后,当欧美国家的乐团出现倒闭或者合并现象的时候,国内还有新的交响乐团在诞生——无锡交响乐团是2023年成立的,2024年底在浙江嘉兴海宁市盐官,还成立了一支大潮爱乐乐团。欧美的乐团主要是靠私人赞助,中国则是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去支持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
和美国茱莉亚学院不一样,天津茱莉亚学院目前只提供研究生课程,而且是聚焦合奏精神和技能的培养,目前设有管弦乐表演、合作钢琴以及室内乐表演三个专业,明年还将新增一个作曲专业。其中前两个专业都和中国市场的需求直接相关。管弦乐表演专业可以给国内80多支职业交响乐团输送人才,而合作钢琴专业的毕业生则可以与其他器乐或者声乐艺术家合作,共同完成艺术作品,去承担歌剧的钢琴伴奏、担当艺术指导等等。国内已有的音乐学院体系都是偏向独奏培养的,我们认为懂得合奏的人才目前还很缺乏。

至于室内乐表演专业的设立,则不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中国目前还缺乏欣赏室内乐的土壤,这个专业也是亚洲首创。歌剧具有故事性,交响乐听起来足够热闹,这在古典音乐当中,是两个较好理解的门类,但室内乐的门槛就高一些了。喜欢室内乐的,可能也是歌剧和交响乐的爱好者,但反过来就未必了。国内基本上也没有全职的室内乐表演团体,或者他们是某个交响乐团的几位成员来组成的,或者参与者是在高校拥有教职的老师,比如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琥珀四重奏。
但其实室内乐的欣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室内乐组合因为人少,更具有灵活性,可以进入咖啡馆、酒吧、图书馆这样的小型空间来演奏,也很容易和观众建立亲密感。波士顿有过一个Chamber Music to Go(可直译为“打包室内乐”)的商业项目,比如你在家办一个活动,就可以下单一个室内乐组合上门来表演。美国室内乐协会(Chamber Music America)也会资助一些不错的室内乐组合参与“乡村驻地计划”(Rural Residency Program),就是让这样的重奏组去到一些几万人的小城市。他们可以举办系列的音乐会,去中小学上音乐大师课。室内乐组合运营成本低,要是让一个交响乐团来做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一方面这个项目支持了音乐家,让他们在深度参与社区互动的过程中得到职业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也让当地人欣赏到了高水平的表演,很多人对音乐的看法从此改变。
中国观众还处于对室内乐慢慢接受的过程,室内乐演奏者也有着一些从事自由职业的可能性,我们很乐于来做前沿的探索。

合奏训练为什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一个从小学习乐器,并以乐器演奏为专业的学生来说,所经历的合奏训练是欠缺的吗?
何为:中国的琴童基本上从小都是一个人来练琴的。就像我从小拉小提琴,要经历一个独自练琴的漫长而枯燥的过程。国外更倾向于把孩子放入一个集体来教学。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挪威小提琴的夏令营,一位老师带着十个左右的孩子在草地上拉一首挪威民歌。歌曲不难,好几处都是空弦,大家在很快乐地边拉琴,边跳舞。我注意到有两个很天才的小孩,拉琴的音色极其优美,十二三岁的小孩,就能拉出那种成年人的音色。音色效果和大肌肉群的配合有关,看得出来他们身体很协调,又处在非常放松的状态。
不过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音准并不好。中国孩子是相反的,音准好,音色不是很好听。音准是一种小肌肉群对琴弦声音的精准控制,是针对基本功来不断训练的结果。这就涉及国内外音乐早期教育的不同。中国会通过那种一对一的教学,让孩子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国外会把战线拉长,并不特别强调在早期一定要掌握这些技能。因此他们觉得让孩子在一个集体里边玩边学是种不错的方式。
今天如果有家长和我说,他们的孩子不愿意学琴,缺乏动力、学琴不快乐等等,我的建议就是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的交响乐团试一试,不要一个人在那里埋头苦练。

三联生活周刊:确实,一些学乐器的孩子也会参加所在学校的乐团。那么天津茱莉亚学院的管弦乐表演专业能够提供哪些更专业化的合奏训练,帮助学生毕业后能够真正进入一个职业化的交响乐团?
何为:我们的管弦乐表演专业包括的乐器种类有长笛、双簧管、圆号、单簧管、巴松管、小号、长号、低音长号、大号、打击乐、竖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这涵盖了构成一个交响乐团的全部声部。如果某个声部有学生毕业,我们一定会再招生,保证是一个齐全的编制。每年的课程,就会围绕天津茱莉亚管弦乐团的排练和演出来展开。这个乐团一年会演约十场音乐会,每场都是不同的曲目。
对于其他的学生交响乐团,一个学期可能就一两场演出,一场演出难度如果很高,排练可能要经历20多次。而一个职业乐团,每年音乐季有那么多场演出,不可能给过多的排练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职业化乐团靠拢,把排练次数严格控制在八次。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完成排练,让每位成员都具备一个严肃认真的排练态度很重要。因为有人就会认为在乐团演奏可以“打酱油”,反正指挥盯不过来那么多人,那么就在一起耗时间。为了建立严肃的交响乐团文化,我们独特的方法是让每位学生的专业课老师都参与到排练当中。所以来到我们的排练现场,你会看到专业课老师要么坐在台下,要么是在台上和学生一起。他们会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生对待排练也不会掉以轻心。
除此之外,管弦乐表演专业的学生还会学习“乐队困难片段”和室内乐演奏的相关课程。他们会变得善于聆听和相互配合,而不是独自演奏。

三联生活周刊:似乎有一种偏见,认为从事合奏的人,技艺水平就不如独奏家。你怎样看待这样一种“刻板印象”?独奏和合奏的技能,是可以相互滋养和补充的吗?
何为:独奏家需要具备一些特质,比如对音准的准确把握、持久的专注力和耐力等等。但优秀的独奏家一定是有合作意识的。即使是独奏,它首先是一种沟通,是把内心的情感用音乐的形式倾诉给观众。我经常会问那些只顾兀自拉琴的学生一个问题——“你想要表达什么?”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观众就不会有共鸣。再有,独奏同样会牵涉到和交响乐团以及指挥合作,比如去演奏协奏曲。我在美国学习时的老师是卡米拉·威克斯(Camilla Wicks),她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独奏家之一了。她就和我说过:“作为独奏家,你需要让指挥与乐团都觉得很轻松。”独奏家来演奏协奏曲,并不是一个乐团来做背景伴奏的卡拉OK。独奏家有时候需要带领乐团,有时候需要衬托他们,有时候则要附和他们。
我在学习小提琴的过程中,感觉进步最大的时期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接触了室内乐演奏之后。就像我的另一位老师所说,“不管你在演奏什么曲子,你需要知道你在哪里(You have to know where you are.)”。什么叫“在哪里”呢?就是演奏所处的上下情境(context)。四重奏的时候,你应该拉多轻,拉多响,这个段落你是在和中提琴对话,还是在和大提琴对话?你是对话的哪一方?这种重奏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拉琴不是随便拉的。即使独奏我也需要知道一个作品所处的情境,比如结合作曲家的传记生平了解它诞生时的情境,这样就知道如何表达情绪。在天津茱莉亚,我们有一位从室内乐表演专业毕业的学生李姈垠,她后来得了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大提琴组的冠军。这就是一个室内乐合奏训练,能够反哺独奏的证明。

同样,参加一支交响乐团的演奏,也能让表演者明白所处的情境。不仅要知晓你在某个时刻是在干什么,还要知道其他声部的演奏员在干什么。对于交响乐的演出,我们会让学生除了看自己乐器的乐谱外,还要了解总谱。甚至还会鼓励那些乐理好的同学,进行“钢琴缩谱”,就是把乐队演奏的部分做成一个钢琴伴奏的谱子,以此对整个谱子有了解,来明确自己的演奏方式。
合奏与独奏是不一样的体验。独奏家是孤独的,那些协奏曲的数量有限,而室内乐的曲目就有太多选择了。偶尔能去参与交响乐团的演奏,比如马勒的交响曲,里面有那么多种音乐色彩,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那种感觉也很让人兴奋。
从精英到大众,一所音乐学院的新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天津茱莉亚学院还有针对青少年的公共教育课程。对于那些对音乐感兴趣,但却不一定会走专业发展道路的孩子,你们希望给予怎样的音乐教育?
何为:关于孩子的音乐启蒙,我被家长最常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孩子应该学什么乐器?中国孩子学得最多的两种西洋乐器,就是钢琴和小提琴。为什么是这两种呢?它们当然是表现力很强的乐器,另外的原因则可以在《虎妈战歌》这样的书里去寻找。那位叫蔡美儿的作者,有两个女儿,一个学习钢琴,一个学习小提琴——这两种乐器都需要自律和勤奋,投入大量的练习时间,像小提琴这样的乐器入门就比较有挑战性。总之,对亚洲“高知”家长来说,掌握这样的乐器是一种智性优越的象征。
但这种选择乐器的“鄙视链”思维,在西方人脑海中是不太存在的。一个身边的例子就是我的同事、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前任首席执行官卜怡明(Alexander Brose)。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学习长号,一个学习萨克斯,都学得很开心。因此为了让孩子能够真正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乐器,同时也让家长走出思维定式,我们为6到9岁的孩子提供乐器探索课程。孩子们可以接触到可能在一个交响乐团里出现的各种乐器,包括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打击乐器、键盘乐器和拨弦乐器等等,进而了解每种乐器的演奏方式、声音的产生原理以及每种乐器的不同音色和音调。在这个过程里,我想孩子和家长都会获得新知,重新来考虑到底学哪个乐器。

我观察到一个趋势是,今天的父母倾向让孩子不要过早地走上专业发展音乐的道路,在他们人生的早期阶段,还是尽可能广阔地去尝试各种可能性。除了“乐器探索”,我们的公共教育板块还有一系列的课程,都是力求让音乐教育成为孩子日常素质教育的一部分。音乐可以让人探寻真正的自我,主动产生与他人合作的意识,可以连接不同的国家和文化。我们的公共教育课程希望让孩子领会到这些音乐学习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很多城市都有音乐厅和交响乐团,但是公众对于古典音乐的认知度和关注度都还不够。身为古典音乐的教育机构,你们也会承担公众普及的工作吗?
何为: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比较特别的是拥有琴童和琴童家长这个观众群体。我们更希望能够走入城市社区,让师生为这个群体带来一些通俗易懂的古典音乐演出。从2025年起,我们启动了一个“城市之声”的音乐会系列,持续在天津音乐厅举办过多场。这个系列,就会从曲目长短、是否好听好理解的角度来做精心地挑选和搭配,可能还会加入天津的特色曲目,例如《运河杨柳青》,让它更本地化一些。
但仅仅迎合观众的需求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引领他们的欣赏能力,拓展未知的领域。从2021年开始,我们每年举办“汇聚音乐节”,会聚焦一位20世纪的杰出作曲家,并追溯其在当代音乐中的传承和影响。像梅西安这样对乐迷来讲如雷贯耳的作曲家,也许一般观众不知道,但如果了解到他是中国作曲家陈其钢的老师,而陈其钢创作过不少耳熟能详的电影音乐作品,就能感受到这里一脉相承的关系。古典音乐不仅是过去的作品,今天这个时代仍旧有一批作曲家在承袭古典传统,继续生产经典。

也许有人会觉得天津茱莉亚学院这样聚焦精英教育的学校,去做大众普及就像是“原子弹打麻雀”,但我认为,正是有学术高度的机构才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是纽约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做的一系列“年轻人的音乐会”(Young People’s Concert),它每期有个主题,像是“什么让音乐有交响性?”“协奏曲是什么?”等等。伯恩斯坦亲自在台上解说和指挥乐团演奏,经由电视转播,这种讲座式的音乐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我会把天津茱莉亚学院比作一个金字塔,而不是象牙塔。金字塔的最顶端是表演艺术教育的卓越,这建立在茱莉亚百年的传统之上;金字塔中间是一个全方位的教育理念,表明了艺术家对社区和社会应该尽到责任;最底端是音乐教育的影响力,意味着能够把最优秀的音乐艺术水准通过理念的更新,让更多的人受益。音乐教育不只是提供给有才华的音乐家,还包括每一位对音乐有兴趣的人。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第38期)

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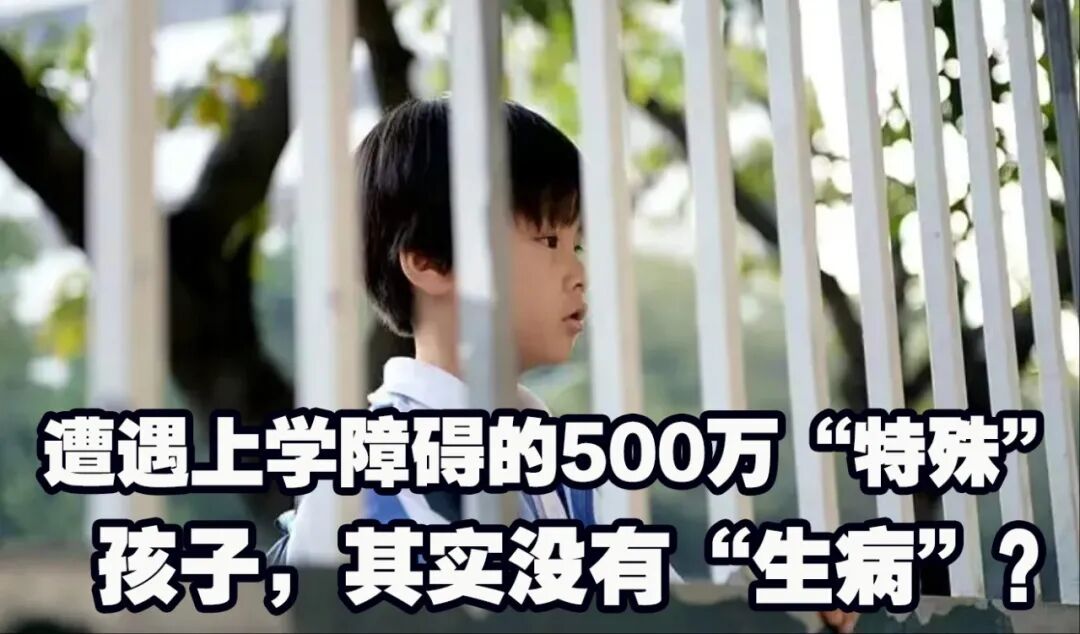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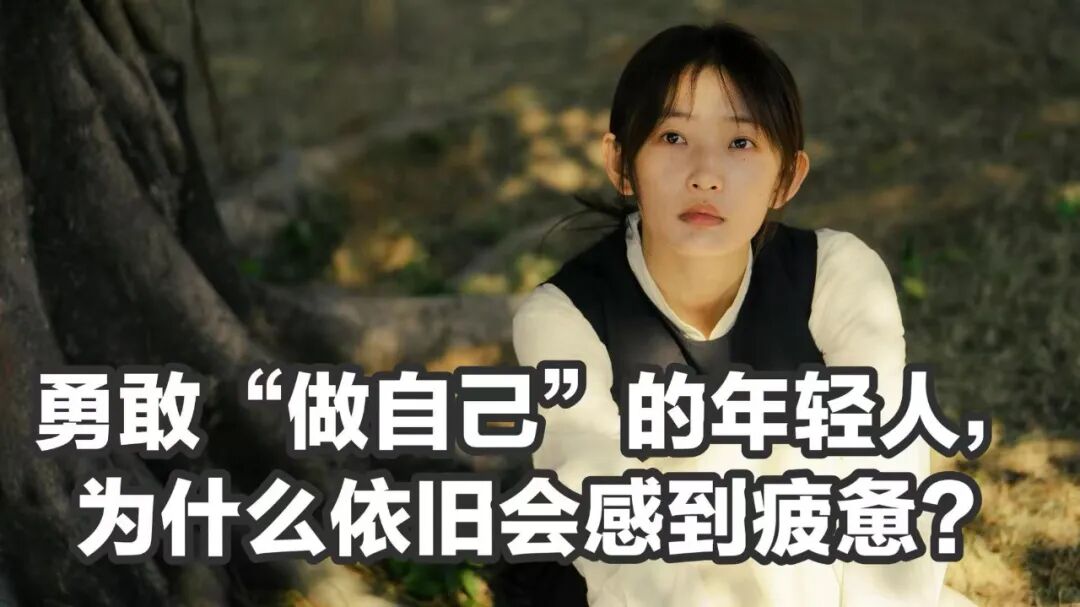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2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50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