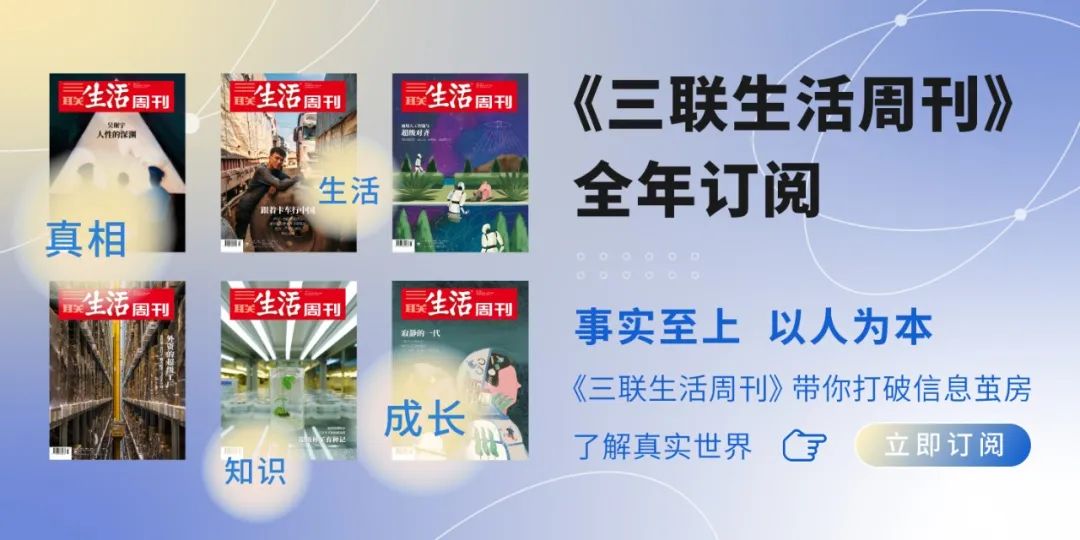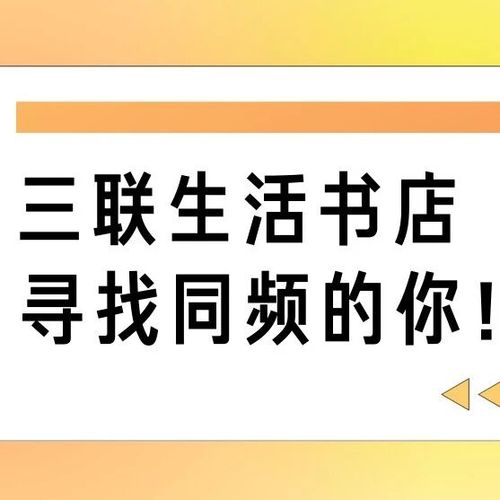勇敢“做自己”的年轻人,为什么依旧会感到疲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8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今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阎云翔到中国的几所高校演讲,分享他对中国“95后”和“00后”青年人的观察、研究和思考。
记者|段弄玉
编辑|徐菁菁
今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阎云翔到中国的几所高校演讲,分享他对中国“95后”和“00后”青年人的观察、研究和思考。
记者|段弄玉
编辑|徐菁菁
作为“50后”一代,上世纪70年代,17岁的阎云翔曾在黑龙江下岬村下乡7年。上世纪90年代,他又回到下岬村从事人类学研究。在代表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中,他描述了激烈的社会变革下,个体日常生活与心理结构发生的微妙变化:个体看似以独立的面貌兴起,但人们并未变得真正自主。
现在,阎云翔的目光聚焦于当下的中国青年——他所称的“Z世代”。在他看来,这一代人完成了此前几代人未曾完成的“内在性转向”,与外在规范逐渐拉开距离,转而将目光投向自我。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杰出教授阎云翔(受访者供图)
与此同时,这种新的自我并未脱离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语境,本质上依然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关系性自我”。正因如此,当Z世代试图“做自己”时,往往会遭遇独特的挑战:在失去传统依托的同时,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安放方式;而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又不得不回归关系性的自我。
以下是本刊对阎云翔的专访。
转向“内在性”的一代
三联生活周刊:您把中国的“95后”和“00后”青年人作为新的观察、研究对象。对比中国以前的世代,他们有什么特点吸引了您?
阎云翔:我觉得他们堪称“横空出世的一代”,完成了前面几代人都没能做到的“内在性转向”。“外在性”指的是个体面向外部的社会环境所做出的决策和行动;“内在性”就是我们内心世界里的情感体验和意义建构。
和此前的世代相比,Z世代更倾向于将自我探索、情绪价值和内在生活作为他们建构生命意义的主要场域。比如说,在建构生命意义时,“80后”青年更在乎的是阶层跃升、个体成就、财富积累等外在性的东西,而Z世代更加注重主观意义上的幸福感受和自我的本真性。
我观察到两个表现。一是很多年轻人开始学习心理咨询方面的理论,参加培训班,开始尝试通过冥想和正念来调整自己。他们开始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内卷?为什么一定要依照传统规定的时间表按时结婚生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他们开始建立了一种新的自我叙事,强调自己不应该被传统的生活脚本所裹挟。

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边界感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通过建立边界,从那些消耗型的情绪或者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实现内在性的追求。要想使这种抽离正当化,就需要一系列新的话语。近年来,“创伤反应”“情感劳动”等疗愈话语之所以会流行,就是因为它们为Z世代所追求的内在性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外壳。
Z世代内在性转向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很强调个体的本真性,简而言之就是“不装”。不管一个社会角色有没有受到社会认可,我不喜欢我就不要扮演,而且我甚至于都不想假装扮演。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了年轻人中的心理热。张鹂在《心灵的呵护》(Anxious China: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一书中描述,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出现了“心理热”,那时人们同样对内在探索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您看来,这两个时代的心理热潮之间,有什么异同?
阎云翔:十多年前的“心理热”聚焦于当时的青年一代,也就是“80后”。他们受到两个外部条件的影响:第一个是成功叙事——“努力就会成功”“爱拼才会赢”;第二是传统的线性人生时间表——对“80后”来讲,人生的关键节点,包括高考、上大学、找一份好工作、结婚生子、买房买车,必须要按时实现。在这两条道德命令的规范下,如果你没做到,就是你不努力,你有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很多人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转向了心理领域。
而如今,Z世代面对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成功叙事开始崩塌,被“80后”所遵循的人生脚本也不再能被复制。Z世代不再将内在性视为解决外在问题的工具,而是将其看作一个价值高于外在性的独立世界,值得深入探索。这是最大的区别。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促成了年轻一代转向内在。养育环境是否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阎云翔:在我看来,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与过去二十几年来流行的育儿方式直接相关,也是其未曾预期的结果。
“80后”的父母处在到处是机会、所有人都能上升的大环境下。但Z世代的父母所处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他们更为焦虑。因此,父母对于孩子的期待也更高,要求他们更加优异,行为上更加端正,不能够惹任何麻烦。与“80后”相比,Z世代作为儿童和少年的自在空间更加缩小,他们从更早的时候就被塑造成乖孩子。
Z世代从小被压抑了儿童的天性,会内化为他们自身的焦虑,最终导致一种“乖孩子”症候。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大学之后,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往往都是乖孩子。因为他们容不得自己犯任何错误,甚至只是没别人那么优秀,他们也一定是自责的。
不过,这批孩子擅长的不仅仅是自我监控与自我责备,他们同时也更加具备自我探索的潜能。可以设想,一个淘气的孩子可能从小就心大,只有乖孩子才会想那么多。如果这些乖孩子希望把自己从那种状态中解救出来,便会很容易就转向情感修复和疗伤。
“自我”的演变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Z世代作为儿童和少年的“自在空间”更加缩小。这好像解释了目前的一种普遍存在的渴望:“寻找自我”。可是,什么是“自我”?中国传统语境里的这种“自我”和西方语境里的“自我”有什么区别?
阎云翔: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语境下的自我,它们都是通过个体之主体性的不断展示并且与大的社会环境以及和他人主体性的互动而成立的。
中国的自我是一种“关系性自我”。个体通过关系来界定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并据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不管是强调社会伦理关系的儒家传统,还是注重人和自然之关系的道家传统,它们都认为现实世界是一种处于变动中的关系的组合,个体则是这些关系中的一个节点。在这种世界观中,最关键的是关系网络的和谐。只有这样,作为节点上的自我才能够找到最自洽的存在方式。而当关系不存在,这个靠关系来界定的“自我”也就不存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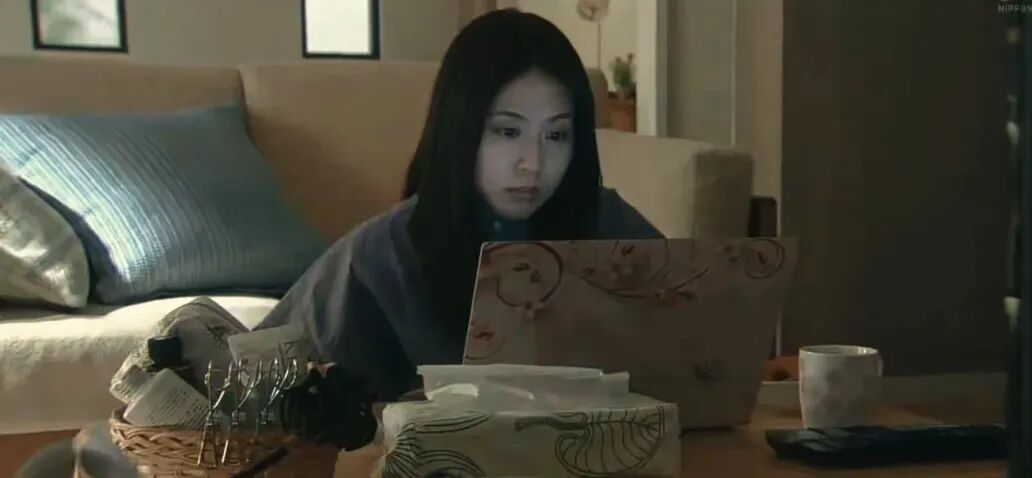
但是,关系性自我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在不断积累的、变化无穷的、无论你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承担的层层关系之下,个体很容易产生一种不堪重负的疲惫感。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自我是一个“实体性自我”。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一个稳定的、自主的存在,但是自我是作为一个公民,或者说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的,它是城邦国家的组成部分。柏拉图则认为,这个实体性存在是靠它那种超物质的永恒的灵魂来界定的,其使命是上升并趋近于非人格化的“善”,但作为肉身的个体却并非独特的实体性存在。基督教认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特的存在,也因此而与其他所有人构成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关系。人能通过内省跟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最终达到进入天堂与上帝共存的理想境地。西方的自我由此而开始了内在性转向的旅程。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之后,这种自我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个体逐步从对上帝的依附关系中抽离出来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实体性存在。笛卡尔、洛克、康德等思想家不断地阐释这种新的自我观,将自我重新定义为理性自主、富有内在道德责任的一种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淡化了关系在塑造自我中的作用,反对人身依附,强调理性的价值远远高于情感。从16世纪开始,将个体界定为自成一体的权利主体的古典个体主义逐渐成为在西方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并进而强化现代西方的自我观。
但这种自我观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个缺点。可以想象,如果自我定义为独立存在之实体的现代西方个体,在精神、心理、情感诸方面都在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道路上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的话,其结果会导致个体的原子化,使其很难建立有效的社会联结。尽管西方社会一直在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和法律来维系社会联结的延续,个体原子化的危险也一直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的自我观只是有所差异,并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各有各的挑战。

三联生活周刊:近现代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很大。当我们现在讲自我的时候,是否就受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个体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西方的影响是如何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相呼应的?
阎云翔: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几代青年对这种思潮的反应。
晚清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这段时间,个体主义最早被引入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当时的“五四青年”试图通过引入和介绍个体主义观念以及现代西方的自我观,来改变传统中国语境下所形成的那种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充分行动能力的个体。
这一时期引入的个体主义理论,主要是以日本为中介的、德国式的个体主义。它强调的是那种无比强大的超人式自我和通过少数超人的内在道德力量来唤醒民众、拯救世界的浪漫主义情怀。这种个体主义思潮很快就和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衔接起来,并融入代之而起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集体主义思潮。
德国式的个体主义有一个内在的弱点,它太强调某些个人的优越性和超人意志,而忽视了个体的权利以及整个群体的力量。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个体主义很快被定义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是不相容的。也因此,在我们这一代,也就是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革命青年”中,个体主义被解释为“以自我为中心”,是一个完全负面的标签。
而在当时宏观的目标之下,中国社会强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完全消解“自我”,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关系性自我”。个体必须从家庭、亲戚、朋友所有这些人际关系中脱离出去,把自己变成新的社会主义公民,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对个体主义的理解又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发现只有个体主义才能够调动个体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渐渐地,个体主义恢复了某种程度上的正当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改革中最早的口号之一。再之后,消费主义进入中国,我们意识到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也可以通过做一个好的消费者来为社会做贡献。但是,市场个体主义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竞争的不断激化和随之出现的攀比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个体越来越焦虑。因为攀比最终是在关系中攀比,个体试图体现自己在整个关系网络中占据了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这种焦虑也体现了中国语境下“关系性个体”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危机,也就是关系带来的重负。
而一旦出现社会条件的转化,比方说经济增长放缓,再叠加关系性个体所承受的重负,它的负面影响就会凸显。在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它的行动者,也就是“80后”或者“70后”青年,而是他们的后继者、还没有获得竞争机会的“95后”“00后”青年,这代青年的反应就是,他们转而开始拥抱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版本,那就是“疗愈式个体主义”:对自己的情绪有特别强的反思性,把疗愈作为人生目标来看待。
三联生活周刊:我感觉,在您描述的“自我”发展路径中,我们好像既没有完全接纳西方的“古典个体主义”,也没有完全抛弃中国传统语境的自我?
阎云翔:是的,前面谈到的演变,正好展示了“个体主义”本土化进程的四个阶段。每一个版本都符合中国特定的文化道德语境,符合我们的现实需求,都是对西方个体主义的本土化改造。值得深思的是,它们从来都没有和古典个体主义实现真正的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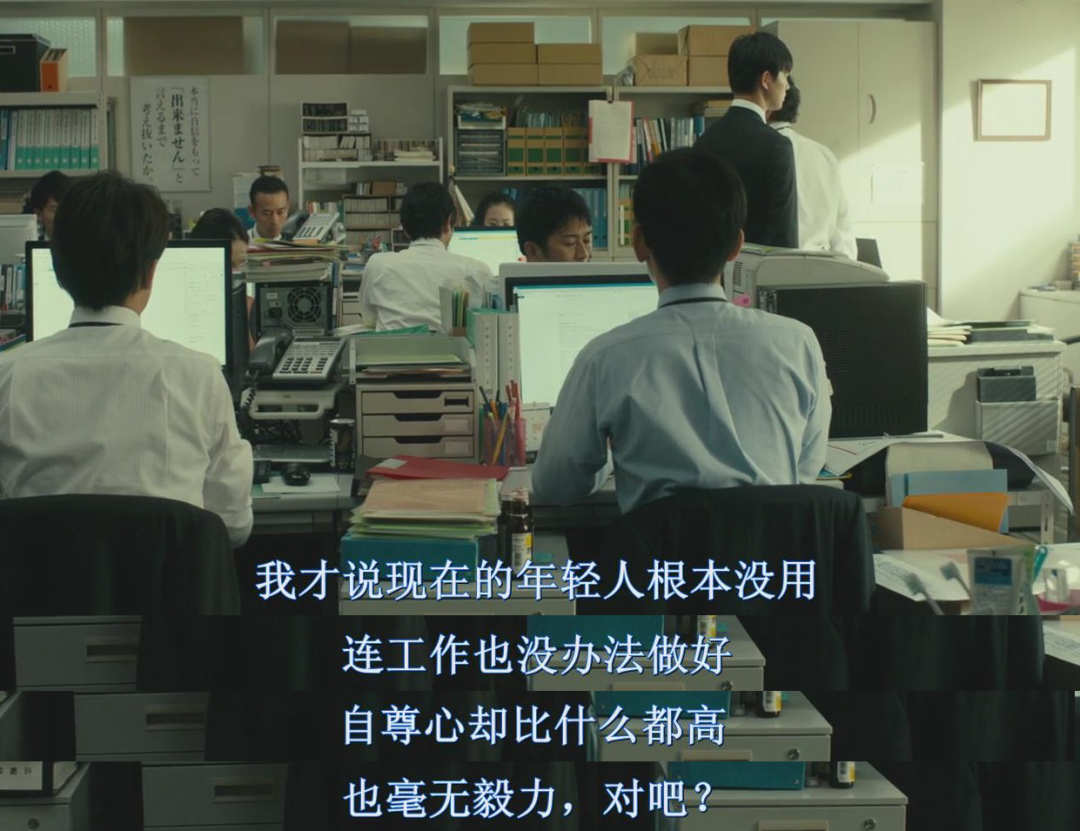
我们对于古典个体主义的理解从来都是片面的,甚至完全舍弃了它最核心、最珍贵的一部分,即作为权利拥有者的个体也必须认同其他个体所拥有的权利、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权责对称、公平正义和尊严等原则。所有这些最终都只能在社会行动层面以个体权利和责任的充分履行这一形式而付诸实施。换言之,权利与责任之平衡是个体主义得以存在的机制之一。
失去传统锚点后
三联生活周刊:您提到的,“Z世代”的“疗愈式自我”,他们有很强的边界感,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关系性自我”?
阎云翔:“疗愈式自我”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强调边界。通过划定边界来达到疗愈的效果。相对于中国传统强调“嵌入”的关系性自我,这是一种近乎革命性的改变。
但到目前为止,这种边界设定的唯一目标就是情绪上的自洽和谐,它的背后没有更激烈的目标,也没有直接和“关系性自我”的传统文化形成对抗。事实上,Z世代并不反对传统的“关系性自我”,他们反对的只是让这个“关系性自我”受到伤害的负面情绪和毒性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父母自然是同盟军的首选,在现实中往往还是唯一的队友。

所以我们看到,与“80后”一代最初对原生家庭的一味批判不同,Z世代在讨论原生家庭时一直保持相对平和的态度和平衡的视角。即使是在网络平台上分享情感创伤的时候,他们也会颇具同理心地看到父母的爱心及其表达爱心的错误方式。不管是通过正面批评还是侧面鼓励,他们希望父母能改变此前的做法,但不要减少“兜底”和“托举”。比如“电子父母”的流行就是一个例子,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看看你做的,再看看人家的父母,你应该向人家学习。这种把原生家庭问题化的做法正是“关系性自我”在Z世代身上的体现。
另一方面,Z世代会勇敢地舍弃那些带来情感伤害的关系,如断亲实践的流行。而这种选择的自主性是从西方的个体主义来的。所以,Z世代的自我是一个本土和外来因素的杂糅。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杂糅诞生的“自我”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到,现在“做自己”这种叙事很流行,但很多人“做了自己”,却依旧感到疲惫。
阎云翔:我认为,“自我性”是个体对于自身所产生的意识和认同,是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这种实践的一个前提就是个体的反思性,他能够跳出日常生活语境下外在性的局限,而静观自己的内在世界。对于Z世代而言,需要思考的是,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做自己之后,他们“做”的是怎样的“自己”。
Z世代不再有传统的锚点来安放他们的疗愈式自我。所以,有些人在真的做了自己之后,即回应内心的呼唤,以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之后,可能发现脚底下是空的,更可能发现自己又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在探寻自我时,Z世代主要依靠网络平台上同龄人群体的支持和共鸣。但问题是,所有的同龄人都处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的相互支持仍然停留在情绪价值的层面,而缺乏伦理、精神、认识论和人际关系等所有其他层面上的支持和升华。做自己的价值观无疑在理想层面直接挑战了传统“做人”的价值观。但是,当价值观被付诸社会实践之后,情况会变得比较复杂。
我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叫作《不讨好的勇气》。这部剧通过一位脱口秀演员吴秀雅的成长,很好地展现了Z世代青年做自己的努力及其遇到的挑战(虽然剧情设在2015年,但剧中的观念和行动毫无疑问属于Z世代)。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剧中主人公说脱口秀、辩论和反思,所有这些行动,其实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展开的:与家人的关系、与脱口秀同伴的关系、与前任的关系,其中无不包含各种权力关系的考量。做自己依然是在社会关系的上下文中展开,不可能离开他人来做自己。

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剧照。自我照料或许足够应对日常矛盾,但在一些时刻,年轻人不得不重新回到传统的关系网络
吴秀雅的母亲来访,并不情愿地透露自己得了癌症。这个消息击碎了吴秀雅那脆弱的自主性——那个坚持要按自己方式生活的女儿,发现自己无法独自承受如此重负。她最终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帮助:前男友郑昊利用自己的职业资源和社会关系为她母亲争取到最好的医疗救治;同时,现男友史野则承担起床边护理的重任。这两种平行的举动揭示了“做自己”的局限之一。自主与自我照料或许能处理日常矛盾,但在生死关头,吴秀雅不得不重新进入义务与关爱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
此外,吴秀雅与男友的关系也展现出“做自己”与“做人”之间的张力。男友是一个自称的“不婚主义者”,坚持在没有制度约束下去爱,而吴秀雅也接受这种立场,将其视为旷野人生精神的体现。然而,在母亲病床前,吴秀雅却承诺要赚钱、买房、好好结婚,给母亲生一个外孙。她母亲不无讽刺地反驳说,别忘了她如今所爱的这个男人是不婚主义者。在门外听到这段对话的史野先是提出分手,认为拒绝婚姻的立场让自己不配成为吴秀雅的伴侣。但后来他意识到,他对婚姻的原则性拒绝本身也成了一种牢笼:他坚持“真爱必须拒绝一切制度”,结果却将自己锁进了另一种教条之中。通过反思,他承认责任与亲密性不可分割。

吴秀雅也面临着同样的道德困境与张力。当她因疲惫与压力而对母亲承诺说,她依然渴望赚很多钱,买一栋大房子,嫁一个好丈夫,给母亲生一个外孙的时候,她将通过脱口秀事业而做自己的那个新自我又重新折叠回了“做人”的语法之中。曾经显现为抵抗的东西,如今至少在话语层面上表现为一种和解。
该剧没有将做自己的过程浪漫化和理想化。吴秀雅的心路历程揭示出:本真性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被义务所缠绕;解放也无法彻底逃避责任。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关系性自我不仅具有现实效用,还具有正当性。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当下做自己,就意味着要从各种关系中剥离出来。
阎云翔:很多人对“做自己”存在误解,以为它只能对应一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完全独立自主的形态。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你就是一种“讨好型人格”,在关系性自我的框架中过得也挺好,而且你也不想改变,那也是“做自己”。
我们关于如何做自己的认知中还存在若干盲点。其一,将做自己误解为完全退出社会关系的网络,如同进入一个无人之境。其二,把做自己想象为摆脱一切责任与义务,从而可以随心所欲、毫无道德约束地行事,最终到达一个无忧无虑的幸福乐土。其三,将做自己局限于叛逆型的思想与行为,而排除了其他可能性。这三个认知误区的共同点在于不了解个体主义价值观的真髓,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了对他人及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还无视所有个体之间平等的原则。

“做自己”的叙事流行于年轻人之间,但很多人“做了自己”,依旧会感到疲惫(视觉中国 供图)
我希望Z世代能够突破这种对个体主义的狭隘和错误理解,为自己,也为这一代人创造出更多元、更宽阔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想成为的“自己”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的。有些人会继续选择做一个关系性自我,有些人则做了相反的选择,还有一些人可能处于两者之间。无论是哪一种,大家都能达成一个共识:只要是出自个体的真实意愿和选择,那就是本真性的自我,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36期封面故事)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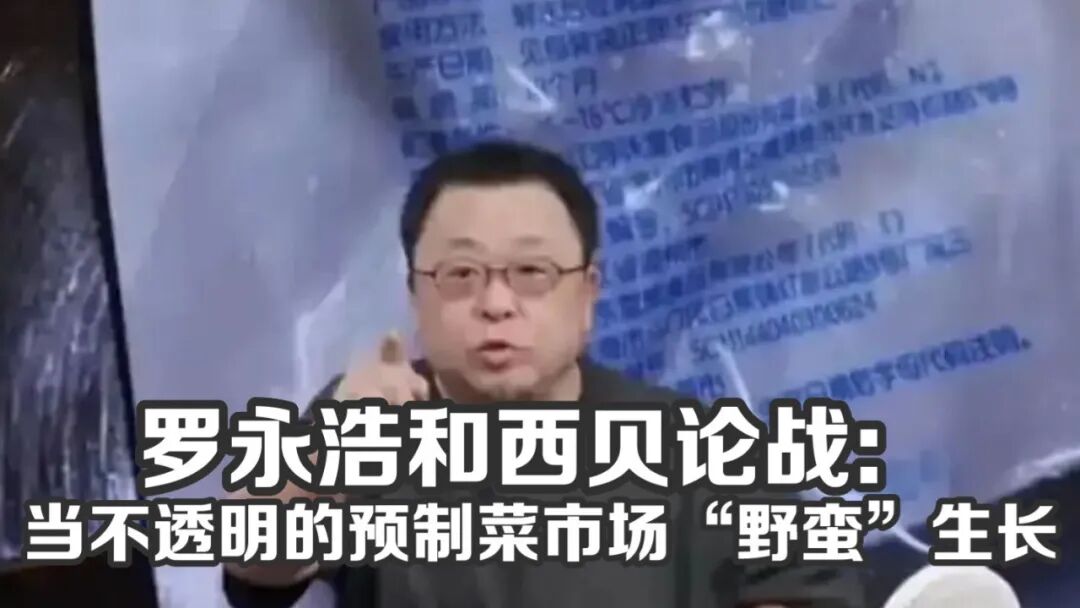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48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