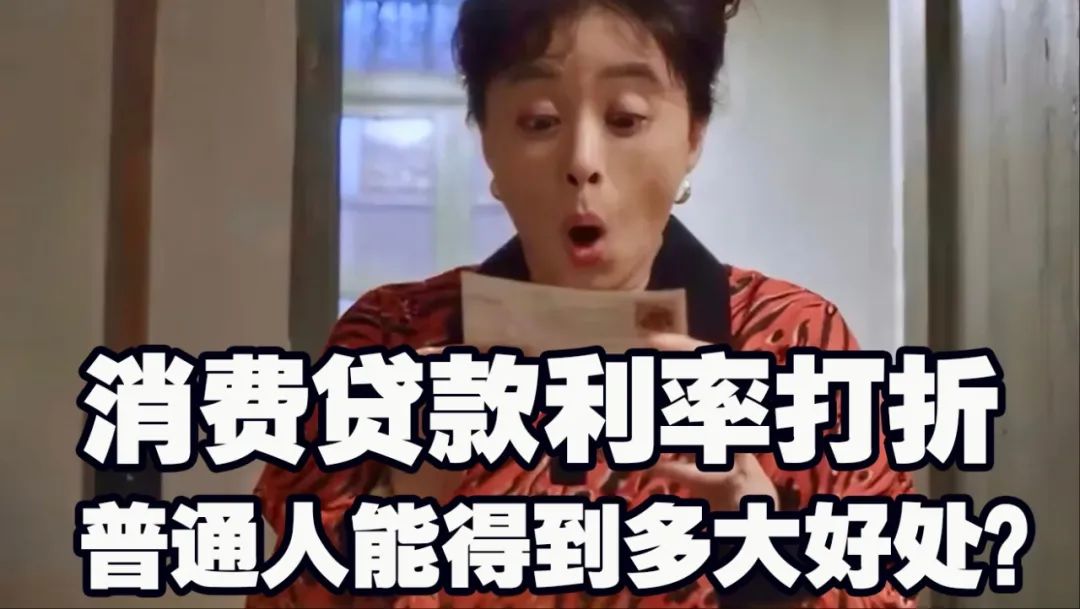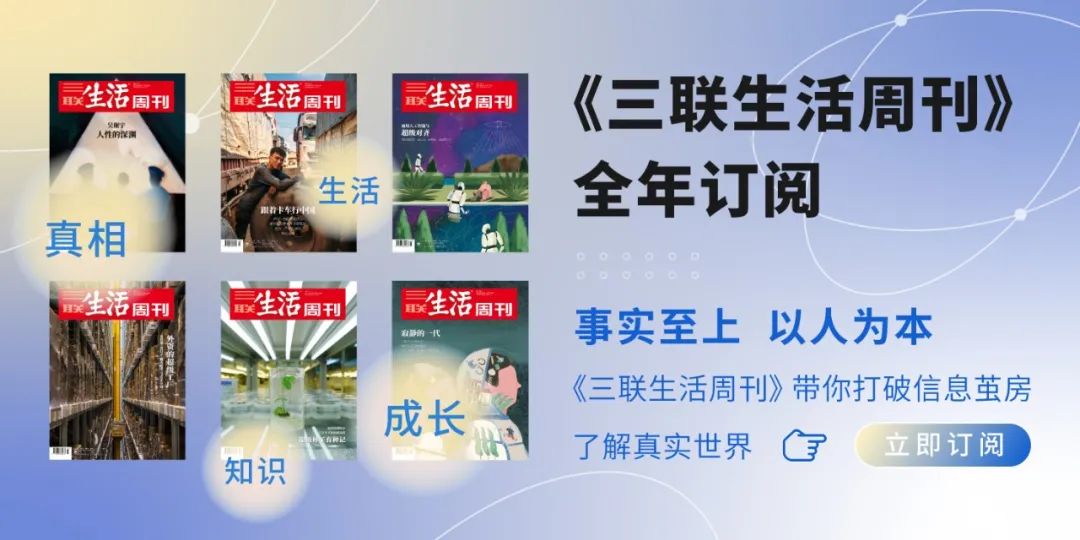暑期争议爆款,什么样的厨师才够“封神”?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8-30·阅读时长18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十六位获得多项殊荣的“大厨”与八十四位灶台尘烟里的市井“小厨”,共同进行厨艺比拼,这样的场景让那个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厨师群像。
文|黑麦
十六位获得多项殊荣的“大厨”与八十四位灶台尘烟里的市井“小厨”,共同进行厨艺比拼,这样的场景让那个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厨师群像。
文|黑麦
这是一档名为《一饭封神》的美食综艺,一百位参赛厨师来自不同的城市,他们的背景不同,烹饪手法也迥异。其中的16位大厨,有着丰富的灶台经验,他们几乎都拿下过米其林星级,算得上是行业中的老江湖;而小厨们大多是“学院派”,有着与大厨们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他们对于烹饪充满热情,却也喜欢标新立异。这些厨师中的大多数,几乎没有出镜经验,也不被多数人所熟知,但最终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和以往的美食烹饪节目不同,《一饭封神》中既没有“治愈的故事”,也不强调夸张的烹饪视觉体验。它似乎剥离了那些被过度消费的情感标签和舞台冲突,反而将焦点纯粹地还给厨师本身。在赛场上,不同代际的厨师,用各自擅长的手法烹饪着“绝对传统”或“奇思妙想”,现场像是把真实的餐饮厨房搬到了节目中。

无论是大厨还是小厨,他们的基本功底都被展露无遗。节目中最小的选手,23岁小厨燃少,将牛奶、蛋白与脑花结合做了脑花蒸蛋;年轻的“光头伙夫”则是用漏勺当锅,在炭火上熏烤米饭;黎大厨绞尽脑汁,最后用惠灵顿牛排的方式制作出了黑牛肝菌,在接二连三的比赛项目,燃少坦言,这是一个“高压赛场”,他感受到了和真实餐厅里一样忙碌的焦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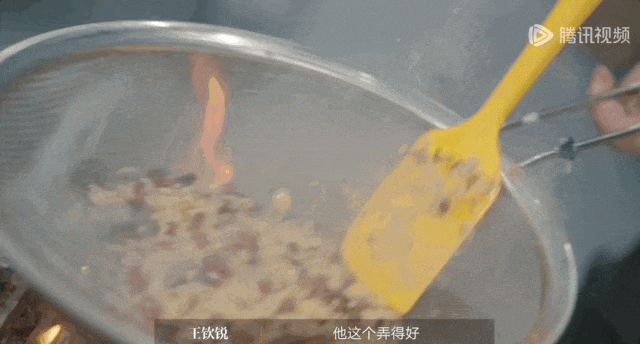
与以往的烹饪节目不同的是,女性厨师也占有不小的比例,从43岁才开私房菜餐厅的蔡孙美华,到知名纪录片《主厨的餐桌》中的“伦敦面条女王”;从专做延边家常味的厨娘,到充满川菜情怀的曾怀君,她们不仅在厨房中展现出细腻的烹饪手法,也用“艺术化”味觉搭配形成创新味道。她们的出现,也几乎让人忽视了曾经这个身份的性别前缀。

当厨师们从具有地理认知性的食材中选材时,传统菜系与新派菜系的比拼便悄然拉开帷幕。同一食材的不同烹饪方式,既映照出厨艺的迭代与风味的推陈出新,也隐约透露出年轻一代对于传统味道与审美的突破。老师傅执着于“古法”、“醇厚”与“传承”,而年轻厨师则试图以反叛打破桎梏,通过“方星墨鱼芦笋卷”和“推沙望月”这两道菜的比较,与其说中餐在年轻一代中式微,倒不如说它正在以一种新的形态重生。


不过,这种对立的冲突在“餐厅挑战赛”时也达到了高潮。在设计菜单时,年轻的厨师小花认为“焗猪扒的味道太过传统”,想在其中加入木姜子调味;随后她又想出把“炸”的做法改成炭烤。她的提议让做了一辈子传统菜的邵德龙颇感惊讶和意外,为此两代厨师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关于这一幕的讨论也由此延伸至社交媒体中。


但无论如何,今日的美食受众都与往日所有不同,在美食视频大爆发的年代,人们仅凭评烹饪技术和菜品的样貌,便可大致判断出一道菜的味道,厨房里也不再有什么秘密而言。由此,厨房的核心仿佛都转移到了做菜的人身上。正如名厨托马斯·凯勒所言,“菜谱是没有灵魂的。作为厨师,你必须赋予菜谱灵魂。”当然,在食物审美日益多元的今天,厨师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厨师阿兰·杜卡斯认为,“最难教的并非烹饪技术,而是一个厨师应有的态度”。那其中包括对手艺的执着,对创新的追求,对食客的尊重,以及对食物的敬畏心。

在节目的一众厨师中,55岁的黎子安意外成为大众的焦点,这个连续8年入选亚洲前50排名的主厨,曾与阿兰·杜卡斯共同工作多年。在厨师比拼的环节上,当众多厨师为一道菜的调味争得面红耳赤时,厨师黎子安却不慌不忙地站在一边,打圆场,偶尔喝上一口啤酒,表现出与场内气氛格格不入的松弛与休闲,这些都与他在烹饪时的气定神闲与有条不紊形成强烈的反差。
专访黎子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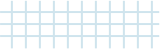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所以你并不是烹饪专业出身的厨师?
黎子安:是的,我在加州伯克利读艺术和艺术史,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想做这一行,我可能需要具备外向的性格,但事实上,我并不擅长那种游戏。因为喜欢和朋友出去吃饭,又喜欢名厨阿兰·杜卡斯,所以我就转行做了厨师。我的父亲当时在经营着一家小餐厅,他很反对我做厨师这个行业。但我觉得艺术和烹饪是一样的,都是关于表达的,我一直认为烹饪比艺术更实用,也更贴近生活本质。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和阿兰·杜卡斯一起工作,他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黎子安:与罗布松(Robuchon)的标准化模式不同, 杜卡斯的每家餐厅都有独特的概念,并高度依赖主厨的个人创造力。他不会事无巨细地控制菜单,而是赋予主厨很大自主权,自己则更像一个把握方向和市场的管理者。这种模式尊重主厨的个性,但也对厨师技术有更高要求。这也影响了我后来烹饪的理念。经常有人问我做什么样的菜,我曾经给过很多种答案,法餐、融合菜、创意料理,但现在我会简单地说,我做我想做的菜。这样,食客就不会在吃之前给一道菜太多预设,而去感受它的味道。
三联生活周刊:你好像总在喝酒。
黎子安:你可能注意到了,我讲话很慢,虽然我没有被确诊过,但我觉得自己有些失读症和ADHD,喝酒能让我达到一种“还可以的状态”。我在节目里喝的是啤酒,日常我会喝威士忌,但我不想喝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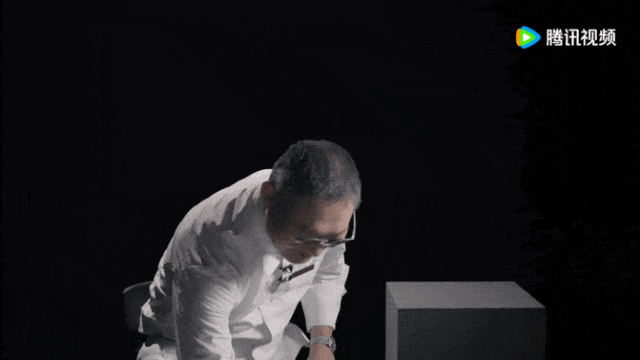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 你有什么想对年轻厨师说的?
黎子安:我从未有过任何厨房的工作经验,所以一毕业就失业,开始在小餐厅里积累经验,起初我做只是厨房的杂工,又没有薪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后来我开始在真正的法餐厅工作,自认为很懂烹饪了,但走进厨房才发现,还要从基础的职位做起。除了厨房本身的压力和文化上的不同,行政总厨总是乱发脾气,像是一种权利的释放。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好的厨师、管理者,经历过挫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被宠坏了,就会变得脆弱。

三联生活周刊:有什么味道是让你怀念的?
黎子安:在我童年时,奶奶留给我很多关于食物的回忆。我们一起逛市场,我在厨房里看她为我做饭,仿佛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样。后来我决定进入厨房工作,她也是全家唯一一个支持我的人。她的拿手菜是港式咖喱鸡,这是她那代香港人融合各地风味的家常味道。
曾经的香港是真正的“不夜城”,工厂轮班、凌晨茶点,街头巷尾永远有人。人们工作辛苦,下班后需要通过吃喝社交来释放压力,这催生了繁荣的街头小吃和夜宵文化。我有一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朋友,他们如今的生活已经非常富足,却依然勤恳工作、毫不松懈。我想,这种状态本质上源于他们成长的环境——那段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在他们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即便辛苦了一天,他们仍会选择坐在街头,吃一份简单的小吃。这些藏在巷子里的味道,给辛苦的人带来慰藉。
但鸡蛋仔、格仔饼、碗仔翅……渐渐从街头消失了,生活节奏变了,人们回家更早,那种因为拼搏而产生的释放需求减少了。更多的人选择在手机上释放自己,由此一些味道也随之消失了,这很可惜。

排版:小雅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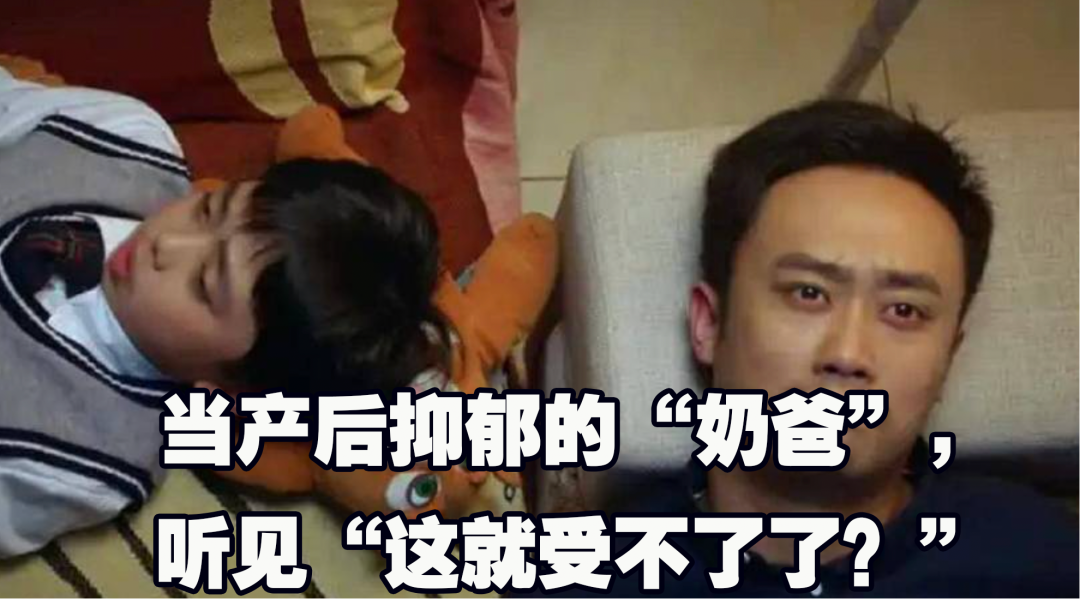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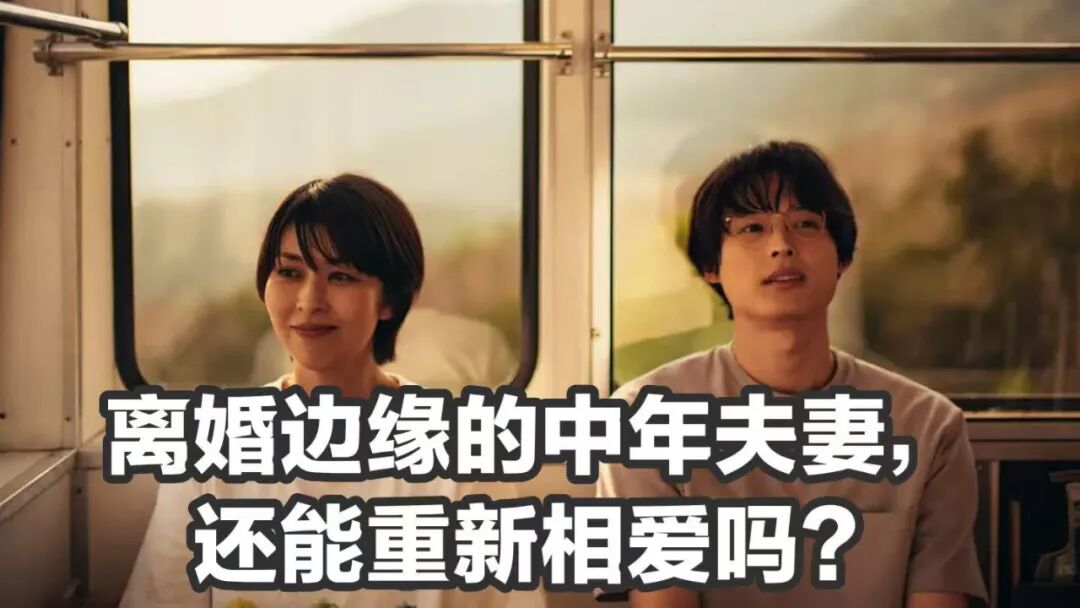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43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