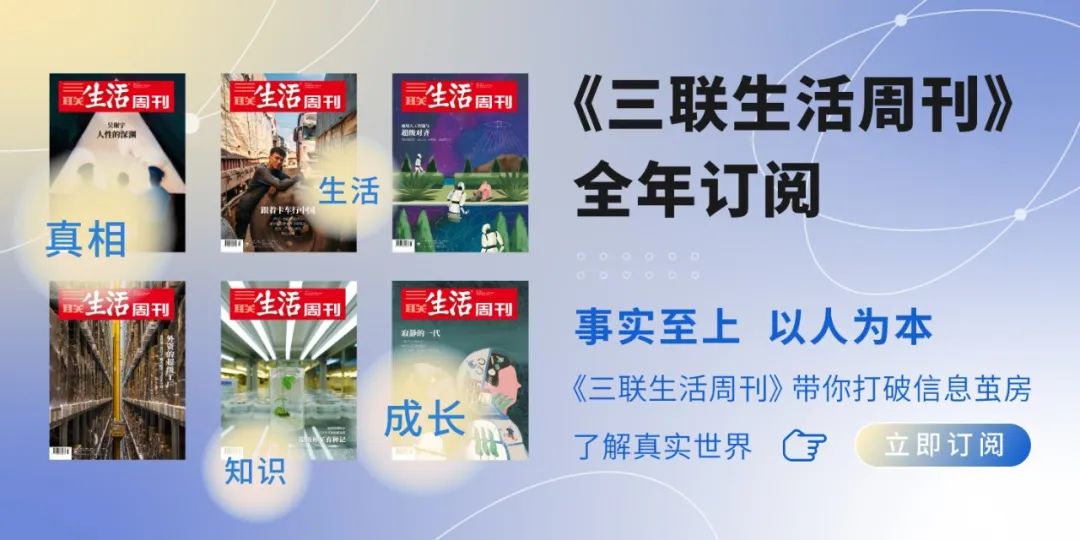中考签约变成“菜市场喊价”:这届家长开始疯狂“跑校”?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6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一年前刚听到“跑校”的说法时,李龙飞觉得很荒唐,他压根没打算参与,“考什么分上什么学校,有什么好跑的”。但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他从北京海淀的南头跑到北头,去了十几所高中,签了好几个实验班。很多学校,他之前名字都没听说过。
学校想争取更好的生源,家长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近年来北京中考出现了“跑校”现象——家长持中考分数,在录取前和学校私下签约。起初,头部学校的实验班以这种方式掐尖,但随着招生竞争的激烈化,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跑校”招生的赛道。今年,在北京中考改革的背景下,跑校越来越像一场“全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选择更多元,也更复杂。
记者|王怡然
实习记者|彭天美
编辑|徐菁菁
一年前刚听到“跑校”的说法时,李龙飞觉得很荒唐,他压根没打算参与,“考什么分上什么学校,有什么好跑的”。但就在刚刚过去的夏天,他从北京海淀的南头跑到北头,去了十几所高中,签了好几个实验班。很多学校,他之前名字都没听说过。
学校想争取更好的生源,家长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在这场“双向奔赴”中,近年来北京中考出现了“跑校”现象——家长持中考分数,在录取前和学校私下签约。起初,头部学校的实验班以这种方式掐尖,但随着招生竞争的激烈化,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了“跑校”招生的赛道。今年,在北京中考改革的背景下,跑校越来越像一场“全民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选择更多元,也更复杂。
记者|王怡然
实习记者|彭天美
实习记者|彭天美
编辑|徐菁菁
跑校:分数交易市场
7月12日,中考志愿填报系统开放的前一晚,卢永华家里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他是北京市海淀区一名中考生家长。过去4天,一家三口连跑10所学校,斩获了6个实验班的“offer”。现在,到了他们抉择的时候了。
出分之前,卢永华对“跑校”都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孩子的补习班老师多次告诉他,要去各个学校问,看能不能签约实验班。出分之后,从来没出过区排1500名的女儿,一下掉到了区排2500名,他一下慌了神,立刻和妻子从单位请了假,中午就开始带着女儿马不停蹄开始跑校,目标从以往的“六小强”(注:海淀区六所知名高中),到压根没关注过的二梯队学校。去之前,他心里还犯嘀咕:“去了应该找谁呀?学校能让我们进门吗?”
去了卢永华才发现,他担心的事根本不存在。学校早就形成了成熟的接待流程。有的在食堂,有的在大教室里,几张桌子围在一起就是一组,每组都有专门负责接待的老师,被家长们围得水泄不通。规模大的学校能有十几个组。过程就像流水线一样简单:报上分数,能签当场就签,分数不够,登记留下联系方式。

《以家人之名》剧照
跑校签约的风潮,在这几年逐渐成为北京中考后的一道盛景。大多学校会在报考前与家长提前签约,进来就保证分到实验班。一些优质生源在“鸡头凤尾”的选择中,会更青睐于“签约条件好”的学校。这个“交易市场”的存在,是学校想争取更好的生源,家长想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的“双向奔赴”。签约是双方的“君子协定”,不具备任何强制效力。但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使交易注定变成一场家长与学校的博弈。
北京中考可分为四个环节,提前招生(“1+3”、集团直升、特长、贯通),校额到校、市级统筹,统招和补录,统招志愿能够填报12个学校。卢永华记得,几乎每所学校的签约条款里都有规定,必须第一志愿填报本校,且不能填报校额到校,否则哪怕最后被录取,签约条款也作废。大多学校要求志愿系统开放第一天上午到学校由老师盯着填报,有些学校还要求填报后立刻更改密码及绑定手机号,防止家长再修改志愿。有些学校发现,签约的学生不来,会按照分数依次往后打电话,来最大限度确保生源。卢永华就在填报期间几次接到之前“够不到”的学校打来的签约电话。
这种生态之下,卢永华也要和学校“斗智斗勇”。他记得去A中学时,老师一听孩子的分数,就把他们带到一个比较私密的小屋里,手机全收上去,告诉他们能签,但要上交学校盖章的成绩单原件。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没了成绩单,之后他们也不再能跑其他学校。那种氛围下,卢永华很难直接拒绝,也不敢当即拍板,他谎称自己要先去看看宿舍和食堂溜了出去。第二天,他去孩子的初中学校,谎称成绩单丢了,弄到了一张新的。拿着这张成绩单,他顺利签约。

《老爸当家》剧照
卢永华觉得,自己是被倒逼着参与进这场交易中的。中考前,他一直单纯认为录取是“考多少分就报什么学校”,不理解跑校的意义。后来他发现,如果不去跑校,孩子就会错失很多机会。他举了个例子:孩子考476分,签到了一所学校的实验班。但这所学校签约时估计得比较保守,最终统招录取分数线就是476,孩子压线进去就能进实验班。一般学校都会在这期间把实验班的名额都敲定,没有跑校签约,按约定填报的孩子,哪怕分数再高,都可能无法进入实验班。
就算签不到实验班,也可能跑出一些优惠政策。“掐尖”之外,为防止生源质量下滑,学校会通过签约时给予一些优惠,来“稳”住录取边缘线的孩子。卢永华在B学校的时候,清楚知道孩子肯定够不上实验班,甚至不一定达到统招线,但招生老师仍给出“如果能够录取,分班考加10分”的优惠政策,鼓励他第一志愿填报该校。有些孩子还可能通过签约去本“够不到”的学校。集团化办学下,有些学校会承诺录取分数线边缘的孩子,只要第一志愿填报该校,后面的志愿可以填报集团内其他分校,也就是“马甲校”——高中可以在本校上课,除了学籍不在本校,其他没有分别。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剧照
事实上,无论去“马甲校”,还是签约实验班,都是不被教委所允许的。马德辉是北京一家中考教育机构从业十几年的老师,他听说有传闻,在出分的当天下午,北京市教育局就紧急开会,要求遏制“签约”的现象,但在家长和学校双向的需求下,跑校这件事还是没刹住车。有家长发现,一些学校会表现更谨慎,不签纸质文件,发一张工资条一样的纸条,家长自己写分数签名,没有盖章、签字等证明,让家长到时拿着纸条来报道。
变化下的2025年
2025年,北京中考发生了几件大事。
今年是北京市中考改革全面落地的第一年。根据新政策,中考科目由原来的10科减至6科,总分由680分调整为510分,占80分的道德与法治采用开卷考试形式,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四科调整为考查科目,成绩以等级形式呈现,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始于2016年的“1+3”教育改革试验项目迎来较大规模扩招。数据显示,这一项目的录取人数从2023年的3144人、2024年的6014人,跃升至2025年的8795人。去年新推出的“0.5+3”集团直升项目,今年在城六区共录取4238名学生,仅海淀区就录取1074人,学生可以在初三第一学期结束后直接升入签约高中,完成3.5年的连续学习。这些被提前录取的学生,不再参与中考区排名。
此外,“校额到校”(注:高中招生计划定向分配到一般初中校)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市相较去年增加了3388个名额,这部分学生参与全区排名,和统招一起填报,优先录取,相当于“提前批”。这些招生方式的变化,挤压了每个高中统招的名额。
总分值变化,参与区排名的考生减少,统招名额缩减,种种变化下,往年的分数和排名都不再具备参考意义,学校和学生,都不知道某个分数,能够匹配上什么样的学校。

《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剧照
因此,今年的跑校,家校双方心里都有没底。学校失去了参考,分数像股价一样波动,甚至每小时都在变。海淀家长李龙飞去过一所学校,老师喊440分以上都去那边排队签约。他看人太多,想先去吃饭,孩子妈妈着了急:“吃什么!赶紧签”。正当排队的时候,或许是学校发现“叫价”低了,签约的人太多,老师又来喊“445分以上才能签”。又过了一天,李龙飞得知这所学校又涨了,变成450分。
在乱局中,考生家庭的信息获取渠道更不透明,于是更为焦虑。而应对焦虑的办法,唯有更积极地跑校。卢永明采取的策略就是“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只要在470-480的分数段内的学校,都先签了再说。卢永明就遇到过一所学校,开始趾高气扬“叫价”483分,不给他签,后来分数一路走低,最后录取线才474分。还有所学校最开始叫价到478分,协商后把女儿签到了第二实验班,妻子还觉得挺走运。没想到,这所学校最终录取线只有462分。他听朋友说,还有学校估的太保守,孩子签了实验班,却没过统招线,家长很生气,认为学校不负责,浪费了孩子宝贵的第一志愿。
这些变化也变相扩大着跑校的范围。李龙飞就是这样卷入这场“战争”的。他孩子分数440分,区排名一万出头。一年前身边就有家长告诉他要“跑校”,去签实验班,李龙飞乍一听觉得很荒唐:“这有什么好跑的,考上哪就去哪呗”。他对孩子要求不高,又觉得“海淀没有差学校”,心里早早定好了目标:考上家附近的一所中学。
孩子中考发挥得正常,按照往年的区排名,上该中学问题不大。中考后,李龙飞抱着“去看看孩子未来学校怎么样”的想法去了那所学校。那天下着大雨,家长们聚在大会议室里,一批批进去。被放进去后,家长依次举手报出孩子的分数,“就像菜市场卖菜一样,每个人报一遍自己的价格”。老师听完,花了几分钟时间快速介绍了一下学校情况,立刻说:“455分以上的来这边,其他家长可以回去了。”他当时就懵了,这就结束了?更令他不安的是,本以为能上的学校,喊出的分数比女儿成绩足足高了15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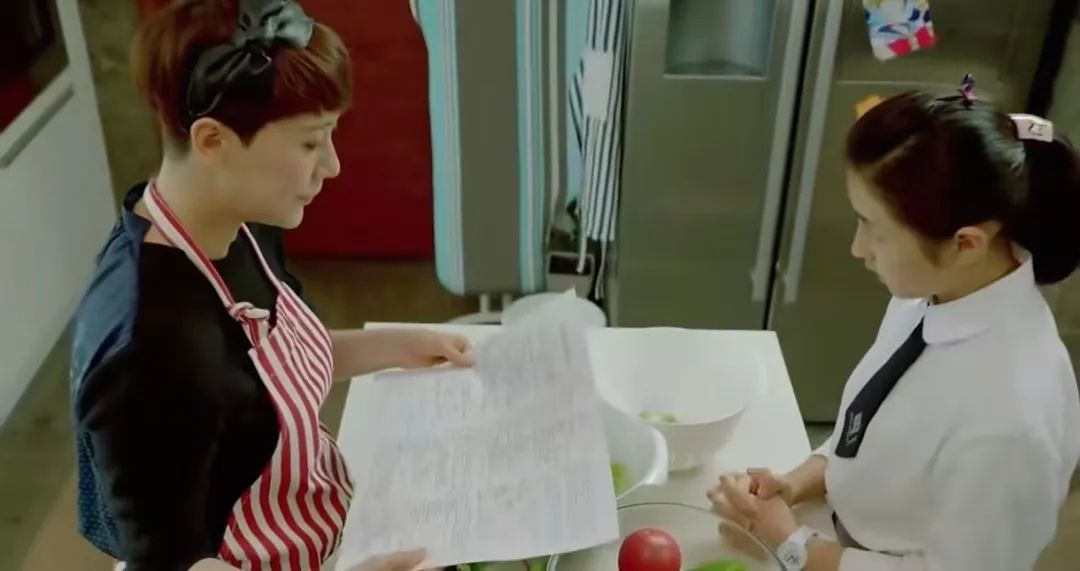
《小别离》剧照
“天塌了,这兜底的都兜不住了?”李龙飞和妻子开始带着女儿走上跑校路,比起签约,他更想知道女儿到底能上哪所学校,还有没有学上,从家附近到十几公里外的学校他都去,足足跑了十几所,很多学校他以前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他发现许多学校都在宣传实验班上做足了功夫,布了很多展板来实验班的师资力量,有的清一色博士,甚至还有院士。有一些录取线低的学校极力邀请,让本没有签实验班打算的他,迷迷糊糊签下了好几个。
实验班
没人能说清跑校这股风是什么时候开始吹起的。在北京一家升学机构负责人刘明印象里,最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出现。但以往,通常是头部考生参与,为签约“六小强”的特色实验班。但今年,他感受到跑校人数明显增加,蔓延成了一场全民的运动。区排一万多名的孩子,也能签到学校。
在马德辉看来,这是学校间互相竞争引发的聚集效应。他举例,按照以往的“江湖地位”,C中学排在A中学之前,但A中学长期有签约传统,吸引走了大量优质生源,实验班数量今年已经扩至6个。或许是这种压力之下,C中学今年也开始接受跑校签约。
“对高考成绩来说,生源是首要条件。开始是一些区重点校搞签约,拿出实验班来争取优质生源,那对于下一梯队的学校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必须也得激进起来,否则生源就很容易被别人抢走了。怎么提升生源?你必须要拿出实验班来,否则大家不会轻易去选你的。”马德辉分析。海淀家长高峰和我分析家长追求实验班的心理,在他看来,不同类别的实验班,师资、课程进度上的差别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同学的质量。“跑步的时候,后面放一只豹子追,和一只狗在追,效果肯定不一样”。

《鸣龙少年》剧照
层层传导之下,几乎每个层级的学校都要搞出实验班。高峰就遇到过一个小型学校,每年只招收七十个学生,只能分两个班,但这所学校在向家长宣传时,介绍自己有理科实验班和文科实验班,鼓励家长签约。
马德辉的观察,跑校在海淀区又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教育资源越丰富的地方,校间竞争越大。在他看来,单纯考虑教学因素,学校间差距没有想象中大,但高中也意味着资源。有的学校和知名大学合作得好,每年“强基计划”名额多;有的学校有“拔尖创新人才”项目,小中大衔接做得好;有的学校以“衡水模式”闻名,高考分数亮眼……
这种情况下,不止学校挑选生源,家长也希望有一张谈判桌,掌握更多主动权。一位今年中考考生的家长在拒绝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太多家长在网上贩卖焦虑了。现在好歹还有个跑校的机会,让你去了解情况,一声令下大家都不许跑了,大家都盲选,那你怎么办呢?”
卢永华说,海淀区一个区就有60多所,在他女儿分数段内的就有10所左右。这个学校管理严格,压力大;那个学校更适合孩子,但“清北率”不高;这个学校最好,但不一定稳录,风险高;那个学校政策好,给了最好的实验班,但去了有些浪费分数……卢永华一家仔细掂量着各种条件权衡着,最后,他、妻子和女儿各持己见,看中了三所不同的学校,一家人又陷入纠结。

《出走的决心》剧照
当越来越多的学校都参与进了生源争夺战之中,花样也越来越多。很多学校把实验班的“班型”分得特别复杂,最极端的情况,一所学校计划招七八个班,只有一个是普通班,其他全是实验班,每个实验班都起了不同的名字,除了师资力量外,还有些课程设置、培养方向上的不同,分数匹配哪个班型,这个班是干什么的,卢永华只能一个个学校咨询过去,到最后也没太搞清。
高峰研究得透彻。从儿子初三开始,他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研究规则、听报考课。今年报考季来时,他俨然自学成了“报考达人”,在网上找他咨询的家长有几百个。“海淀是一个把学生层级划分得特别细密的地方”。他介绍,现在各校实验班花样百出,比如某校“某班”,在今年分为“某1”、“某2”、“某3”。但无论名目,底层逻辑就是按分数划分的“一二三四类”实验班。他分析,这样做的本质,就是以前只“掐尖”,现在需要吸引各个分数段的学生,扩大挑选范围,最大程度地保证整体生源,避免录取排名下跌影响未来整体招生质量。他在推算各校今年录取分数线时,最重要的两个参考指标就是该校上一年录取的最低区排名和当年高考分数。
抉择
“就像看电影的时候,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都跟着站起来,最后谁也没受益,但谁都很辛苦。”李龙飞在跑校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一路按部就班读书,从老家考到北京,如果不跑校,他不知道教育现在这样复杂。虽然签下了好几个实验班,他最终没有履约任何一家。对他来说,实验班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师资、资源好,但意味着竞争也更强。
“我们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哪怕没考上大学的人过得也都挺开心的。但现在考上‘985’都不算好大学,我能感觉到,孩子从初中开始一直处于一个不开心的状态。”李龙飞的女儿初中在一所崇尚自由成长的学校就读,但每天写作业仍要到后半夜,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想到跑校时,被够不上的学校拒绝时女儿的失落,李龙飞不想再给孩子任何压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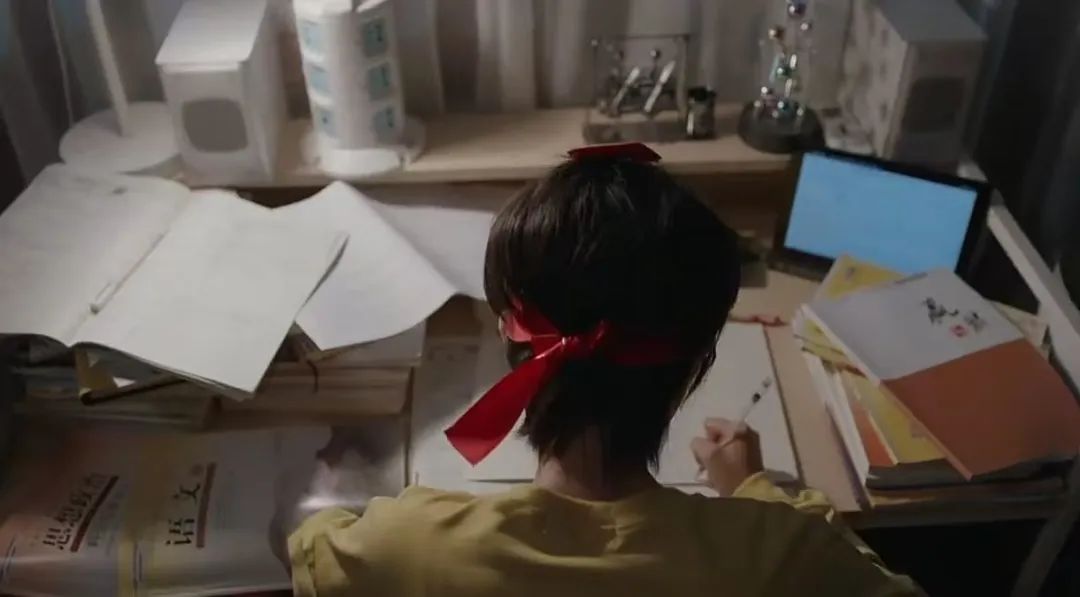
《少年派》剧照
“一分一操场”,因为跑校,卢永华对这句话有了实感。他见过不少家长,因为孩子分数不够被保安拦住,校门都不让进。家长和孩子站在门口,不死心地问着:“我们过两天再来行吗?”“我能不能先登记一下,之后可以再联系我?”看着他们被拦住后的不知所措和尴尬,卢永华心里涌起一股物伤其类的悲哀。
他自认为并不是“鸡娃”的家长。女儿小学在昌平读,为了让她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买了海淀的学区房,但又担心女儿在海淀一下跟不上,只选择了一个很普通的初中。孩子自己懂事听话,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十,每周只补三节课。在卢永华的圈子里,这堪称“佛系”。女儿有同学从初三开始就不来学校上课,一整年都在外面的补习机构“冲刺”提升分数。
这样的氛围下,卢永华不想浪费女儿辛苦考出的分数,可6个offer摆在眼前,每个选择似乎都有些不太满意,一家人决定听女儿的,填她最喜欢的学校。但直到志愿截止填报前,卢永华还是有些不甘心。纠结中,他想,要不搏一把“校额到校”?填报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那几天,一向热闹的班群里鸦雀无声,没人会交换信息。他从老师口中打听出来,孩子中考校排15名,他盘算着孩子前面同学的分数,揣度他们的填报方式,觉得有冲刺的机会。这就是一场赌博,填了,之前所有签约条约都会作废;不填,孩子就彻底与“六小强”无缘。

《小舍得》剧照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女儿最终录取了一所“六小强”学校的普通班,而女儿心仪学校的统招录取分数线比孩子高了一分。
跑校的战争中,每个家长的想法都不一样,我最好奇高峰是如何选择的,毕竟他研究报考的初衷就是“每一分都是孩子辛苦考出来的,做家长的不能浪费”。到底什么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在三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多次试图询问高峰孩子的分数和录取情况,但他每次都神秘地笑一笑,然后转开话题。
最后他只告诉了我一点:他没有为孩子签约任何实验班。高峰统计了前几年的规律,学校的分数“叫价”一般都是由高到低的。7月13日志愿填报开始前,他待价而沽,准备等到开放志愿填报后,再和学校好好谈。
快到报志愿的尾声时,高峰终于敲定了一所学校。没想到,妻子坚决反对,没看上这所。他对此颇有不满:“我研究了一年,她只看了三天”。
他们都无法说服对方,决定在签约现场给去上补习班了的孩子打电话,听听孩子的意见。
“那孩子自己怎么想?”
“他说,都行。”
(除马德辉外,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排版:小雅 / 审核:同同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大家都在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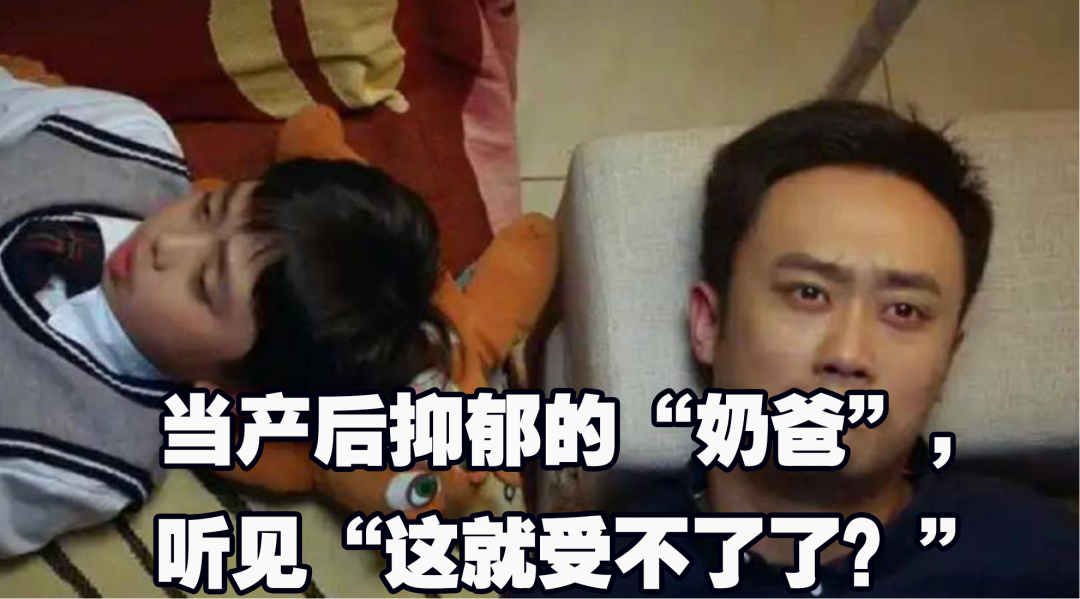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4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6139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