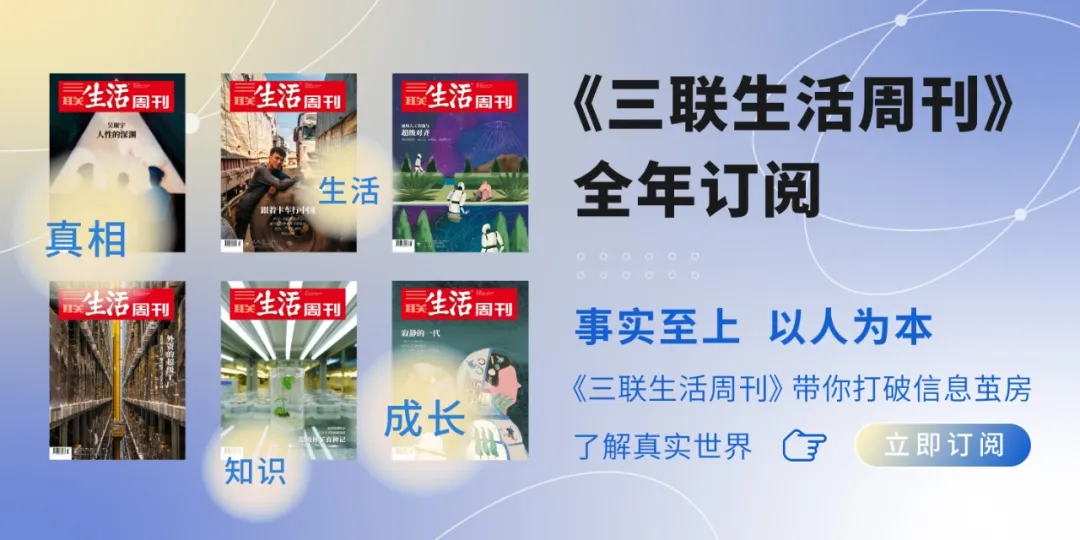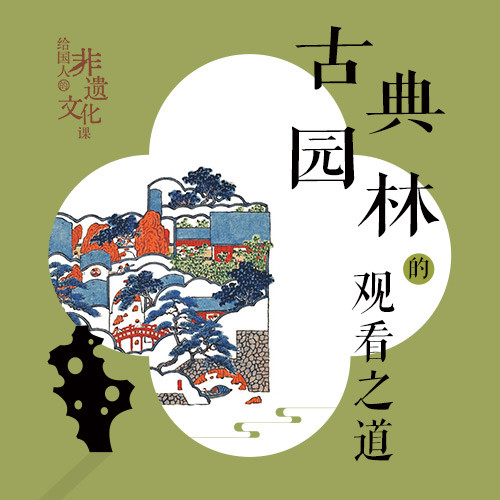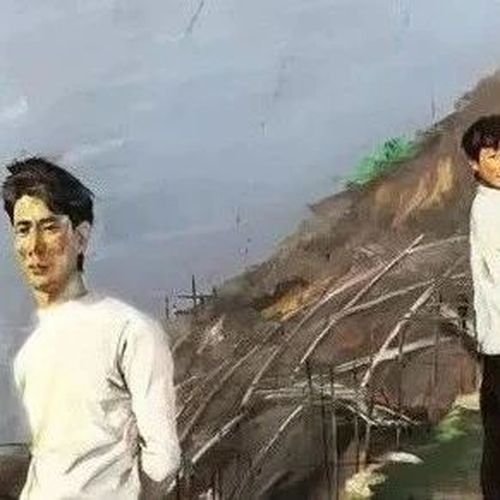19岁,我独自处理了父母的丧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0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口述|余时安
作者|胡怡靓
11天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那天我从学校回来,和妈妈约好她来高铁站接我。在车站等了很久,一直没看到她,手机也打不通。后来我终于打通家里很久没用过的座机,电话那头传来妈妈微弱的声音。
 《世界奇妙物语》剧照
《世界奇妙物语》剧照
她以为自己只是低血糖晕倒了,让我打电话给爸爸,幸亏除了打给爸爸,我还坚持打了急救电话。后来听邻居说,救护车先到,打不开门,犹豫要不要破门,爸爸正在赶回家的路上,让他们暂缓破门。
爸爸到家后,妈妈被紧急送医,初步判断是中风,被送到脑神经科接受治疗后依然迅速恶化,四天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她右半边身体几乎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认知,只能在我和爸爸探望时拉着我们的手,努力挤出一个歪斜的笑容。
她的颅内压不断上升,医生不得不为她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入院时,为了融化肺部血栓,她本来服用了抗凝血药,此时也停了,随后被转入重症监护室。第一次开颅手术中,医生就发现她的血液有些异常,但由于检查报告尚未完全出齐,具体情况不明确。第二次开颅手术前,医生发现她的白细胞异常,随后查出妈妈还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在中风、肺栓塞、白血病三重打击之下,妈妈无法再化疗,也无法服用标靶药(即靶向药),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本细小的栓塞一点点变大,堵塞心脏和血管。此时,妈妈也不能再做手术摘除死亡的脑组织来减轻颅内压了。
香港的医院不需要家属24小时陪护,只能在固定时间探视。妈妈住院那阵子,我和爸爸轮流去看她。爸爸蔫蔫的,看不出情绪起伏,我跟他说妈妈想喝什么汤,他就简单煮一煮。偶尔我和他聊起妈妈的情况,他总是说,别想了,也别说了。
但有一天,我把妈妈之前做的菜倒掉了,他忽然生气,问我:“你为什么要扔?扔了,是不是这个人就没了?”他说我这样做不够避讳,不够讲究避谶。最终,妈妈在入院10多天后去世。妈妈去世那天,爸爸少见地嚎啕大哭,以后就开始每天吸烟、失眠,我有时只能陪着他一起睡觉。白天,我们也一起出门、一起奔波于各个政府部门,处理后事、填表、提交资料。他很少和我说话,不停地抽烟,我们两个好像都很茫然,他没有跟我谈起今后的生活安排,我也没问。
 《入殓师》剧照
《入殓师》剧照
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你晚一点可以养只小狗。我以前就挺想养狗的,爸爸这么说,我就开始上网查各种狗狗的品种,一只一只问他:“这个算不算小狗?”
妈妈离开11天后的凌晨,我被剧烈的喘息声吓醒,发现是爸爸发出来的,他已经人事不省。我马上对着他大叫,摇晃,结果都毫无反应。我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在救护员指导下将他从床上拖到地上,进行心肺复苏。
把爸爸拉到地板上我才发现,他眼睛通红,脸色黑得吓人。我持续进行了十分钟的心肺复苏后,救护车和警车终于到达,急救人员接手急救,使用电击仪器和心外压机器尝试抢救。最终,在医院的急救室,医生用了强心针和肾上腺素后,爸爸暂时恢复了心跳与血压。医生告诉我,爸爸是突发心肌梗塞,因为心脏停止跳动将近半小时,时间太长,脑部已严重受损,失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只能靠医疗仪器维持生命体征。
在爸爸抢救的时候,我不敢睡觉,害怕一觉醒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晚我甚至忘了带手机,就跟着救护车匆忙赶往医院。
入院的第二天下午,爸爸第二次停止心跳,急救成功不到半小时,又发生第三次心跳停止,八分钟后,依然未能恢复。医生从急救室走出来,问我还要不要做复苏,并表示此时复苏意义已不大。我决断不了,把这个“权力”交给了电话里的亲戚长辈。我跟他们算不上十分熟悉,但此时让他们来做决定,心里会好受一点。根据亲戚的建议,最后我和医生说,如果急救30分钟后仍无反应,便放弃急救,保留相对完整的遗体。
父亲最终没有醒来。
发生这一幕时,我独自在医院,面对爸爸的遗体,我以为医院会立即处理,就坐在病床前等着负责的护士。等了好久,一抬头才发现,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爸爸的双腿和颈部都出现了紫色斑点。但在仪器辅助下,他的胸腔仍然有规律起伏。强烈的反差让我极度不适,我走出病房,请求工作人员尽快进行遗体处理。后来我才知道,医生以为我要等爸爸的亲戚从外地赶来后才收殓,所以没有做任何处理。
“果然发生了”
母亲去世后数日,我认领了她的遗体——头骨严重变形、面部冻得通红。谁知道几天后,我又认领了鼻孔和嘴巴被棉花塞住、脸部变形的父亲的遗体。在香港,火化需要提前预约,所以认领遗体后,一般还要等上半个月左右。爸爸出事后,我把妈妈原定的火化时间改了,让她跟爸爸一同火化,葬礼也能够一起办。
在殡仪馆时,我看到由遗体化妆师整理过的爸爸妈妈。他们穿着灰色西装,盖着往生被,面容安详,像蜡像一般,已认不太出来原本的样貌。后来我看电影《破·地狱》,影片里讲到,有些人会在逝者离世后摸脸、换衣服、擦手……而我在父母去世时,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没打防护,不能碰”,我很听话,什么都没做。
我常常会想,在把遗体从冰柜中取出、更衣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骨头会不会被弄断?在医院里躺了那么多天,会不会生出压疮,会不会感到疼痛?那些画面让我像在远处陪伴他们走过了一程,弥补了我因为害怕而错过的细节。
2023年7月19日,我亲手按下了火化的按钮,一切化为灰烬。
 《破·地狱》剧照
《破·地狱》剧照
我曾在网上分享过自己的经历,有不少人觉得,我19岁独自处理这些变故,很有主见。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很有主见的人。我只是已经在脑海里无数次推演过这种情况了,甚至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果然发生了。”
我父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生我时已接近四十岁,爸爸还患有糖尿病,所以我从小就隐隐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了,我该怎么办?他们睡觉的时候,我常常盯着他们看,想着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几年前,在家里的长辈接连生病、去世后,我开始格外担心父母的身体,还建议他们买一块带健康监测和跌倒报警功能的手表。我反复提起,他们反而有些不耐烦,说:“有空就去看,迟点再说。”那种功能齐全的健康手表要上千元,直到他们去世,也没买成。
他们对健康一直不太重视。记忆里,除了爸爸会定期抽血复检糖尿病,爸爸妈妈都从未做过一次完整的体检。但事后回想,妈妈突然中风并非毫无预兆,她身材偏胖,长期受关节疼痛困扰,脚也常常浮肿。我原先以为,她的浮肿是干体力活太疲劳引起的。但实际上,她的免疫系统可能早已出现问题。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三悦有了新工作》剧照
我妈妈是闽南人,上世纪9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我爸爸原本在内地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后来也跟着妈妈一起来了香港。妈妈和爸爸在香港换过不少工作,基本都是服务业。他们都做过保安,后来又先后去了同一家医疗机构当综合服务员,照料病人。因为工作时间相对灵活,同事年纪相仿,他们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比较长的时间。五十多岁了还在做体力活,一个月工资也不高,爸爸常念叨:“早知道当年就不来了。”他说如果当年留在内地,如今每月退休金会跟现在的工资相当。
我家在香港没有亲戚,和社区的连接不太深,不像那些老居民,对彼此、对社区里的保安、菜市场的摊贩都更熟悉,也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交圈。不过我妈妈还算是社交活跃的人,时常和朋友、同事一起吃饭,有人找她帮忙,比如调个班、代看店,她也几乎从不拒绝。家里日常生活中一些事情,比如邻里关系和同事间的人情往来、安排家务,基本也是妈妈处理。
但实际上,妈妈在生活中并没有太多主见,很多决定都会征询爸爸的意见。爸爸的老家在中部地区,他本来不算特别内向,但粤语一直说得不太顺,到了香港后,语言不通,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在家里,我通常跟妈妈说粤语,跟爸爸说普通话。除了在家写字和玩手机,爸爸几乎没有别的爱好,也很少和其他人来往,她已经习惯了通过妻子跟世界产生链接,一旦妻子不在了,就变得难以独自面对生活。
所以从妈妈住院到死亡,所有跟医生的沟通,都是我负责的。好在医院的社工给我提供了一些操作和流程上信息,包括可以申请哪些服务。香港公立医院的门诊、住院、药物和急症室的收费基本都是固定的,定价也比较低,不使用自费药物的话,通常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因为不想麻烦别人,爸爸也没有把家事透露给同事或者朋友,甚至不太愿意通知亲戚们。后来我还是给妈妈那边的亲戚打了电话,原以为他们会赶来,但他们都说家里很多事,来不了——可能当时也没意识到,情况已经那么严重。后来爸爸住院,我也马上通知了那边的亲戚,他们从内地赶过来了,但没有在香港生活的经验,处理银行账户,安排身后仪式、处理社交关系、梳理家庭琐事,一个一个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慢慢去解决。
但我其实从小就不太擅长与人交往,身边也几乎没有朋友。我曾经总觉得,只要能抱抱妈妈,一切还能坚持。等爸爸妈妈去世后,我反复想过,是不是我做得更好,爸爸妈妈就不会那么快去世了。后来我也跟香港做丧亲支持的社工聊过,他们告诉我,这是面对失去时的自然反应,不必苛责自己。
“我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在父母去世以前,我就感觉到,自己正逐渐失去跟世界的链接,非常孤独。
我小学时一紧张就控制不住地眨眼,甚至有些抽搐,有些同学觉得我有点奇怪,话多,渐渐开始疏远我。我有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在小学时,有个朋友告诉我,和我聊天其实挺开心,但因为别人的眼光和压力,她不敢跟我走得太近。小学毕业露营,大家即将分开,她哭了,我递给她一张纸巾。其他同学立刻叫我不要递纸巾她,她根本不想要。在大家的起哄中,她嫌恶而抗拒地跑开了。
因为小学时成绩不错,我升入了一所不错的初中,但境遇却没有因此好转,甚至越来越差。我明显感觉到,很多人拿我取乐,我好像只能成为团队中的小丑角色,才能生存下去。有一次,老师要我去组织一个集体活动,大家都不想参加,就开始排挤我这个组织者。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担任过班干部了。
到了高中,我在学习上开始“摆烂”。高考那段时间,我每天上补习班,一边愧疚,觉得自己在浪费钱,一边又持续睡觉、玩游戏。我妈对这些都看在眼里,却装作没看见,仿佛我还很努力。
小学时,我的父母会给我升学意见,比如我想读女校,他们认为男女混合制的学校更能锻炼和异性相处的能力。但到了中学之后,父母也不能给我建议了,关于学习的决定,基本都是我独自做的。
我和妈妈偶尔会聊到我在学校里的社交,她总是说:“别人不喜欢你,肯定是你哪里不对。”听得太多了,我就不谈了。我去看过心理医生,想证明给妈妈看——你看,我真的很痛苦。但未成年人看医生需要家长陪同,于是我告诉妈妈,自己的偏头痛和耳鸣很严重,她以为是压力引起的,陪我去看了一次。医生并没有给我下诊断,我也没有好好吃药,没坚持做医生布置的功课,这事就过去了。
离开香港上大学后,我的人际交往稍微好了一些,虽然仍然没有亲密的朋友,但起码做小组作业能找到队友了,还有同学能帮我交个作业、传个笔记。
父母去世后,我好像没有什么非常崩溃的瞬间,但不敢一个人在家过夜,我感到强烈的无助、焦虑。回到学校之后,我找了很多校内的心理咨询师,他们有的会反复问我,为什么感受不到我的情绪,有的咨询师则暗示,是我对妈妈的忽视,导致父母去世这一系列事情。聊了一阵后,我开始觉得,既然没什么改变,先休学是不是更好。但是亲戚们都不太支持。他们劝我不要沉溺在悲伤中,不该要求别人,应该收敛情绪,做好眼下的事情。我照做了。
 《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悲伤逆流成河》剧照
在香港,我家一直住的是公屋,有点像内地的廉租房,父母去世后,人口减少,我需要从原来的公屋搬到一个更小的公屋。新的住所空间有限,我只带了一些必要的东西,比如家电、衣物等。可能希望有个新的开始吧,我没有刻意保留过去的痕迹,父母的遗物也只留了一部分,比如妈妈以前常用的包包。
爸爸妈妈就葬在香港。除了特殊的日子,我现在大概每半年会去墓地看他们一次。虽然父母以前也未必真的理解我,但只要他们在,能说说话,有人作伴,就还是一个家。如今一个人,那种孤独的感觉很难形容。
香港是个很忙碌的城市,地铁一直运行到凌晨一点多,我之前实习,晚上十一点多下班,地铁车厢里仍然有很多人,有时甚至连座位都没有。香港也是一个边界感很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被切割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很难变成朋友。在这里,我常常觉得,人好像只剩“工作属性”了,脱离工作,你就没了位置,没了角色,无所着落,非常渺小和颗粒化,个体好像是不存在的。
我下班时间比较晚,回家之后就一个人看看小说,刷刷手机,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当然,香港是个很方便的城市,遇上什么困难,往往可以找相关的机构帮忙。也因此,个人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制度和服务体系的。因为住房面积普遍较小,香港人已经习惯了以小家庭为单位生活,没结婚时和父母住,结了婚就搬出去住,生活上的问题,也通常在这个小家庭内部消化解决了。当然,日常生活里,大家在小事上挺热心,搭个话、帮个忙还是不难得。
我还没谈过恋爱。我挺想有个伴的,不一定是恋爱或者结婚的关系,也不奢求“灵魂伴侣”的亲密,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共同分享一些情绪,一起经历事情,像个“锚点”,让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不那么薄弱。
 《路过未来》剧照
《路过未来》剧照
有时候坐地铁,能看到一些约会软件的广告,有面向年轻人,也有面向中年人的。所以如今找个“恋爱搭子”并不难——可以一起吃饭、逛街,体验一些短暂的快乐,感受多巴胺的分泌。但要找一个真正三观契合、能建立长期关系的人,那就复杂和困难很多。尤其在香港,结婚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素质教育几乎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奥数、珠心算、音乐、英语、体育等等,每一样都对应着昂贵的辅导班和培训。
我现在和妈妈爸爸那边的亲人联系比以前频繁,有时候一两个星期就会打个电话,聊聊近况,在学业或职业选择上,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往爸妈在的时候,我们总是一家三口一起过年,如今过年,我会去父母两边的亲戚家,比一个人留在香港好一些,不那么孤单。
爸爸妈妈的亲戚现在会共同资助我一部分生活费,我也靠网上发布信息做约拍维持开销——帮人拍照,记录他们的生活。每次拍摄,都要和一个家庭、一对情侣、或一个个体沟通,对我来说,算是我与这个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我想努力不再让自己的生活再度变成一个真空层。

排版:秋秋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9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