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里受挫的孩子,在网络游戏里寻找认同和“社交价值”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4-18·阅读时长19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李涛长期关注乡村教育,曾经在中国西部的农业县——四川芥县(化名)开展了三轮田野调查。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对于乡村的孩子们而言,网络游戏已经超越了娱乐和休闲的功能,是一种社交货币,甚至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乡村社会的衰落,让乡村孩童在生活中面临更多无意义感的境地,在现实与虚拟的交织中,他们在网络游戏中构建自己的身份与价值。
以下是李涛的讲述,部分据其公开发表文章、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整理:
口述|李涛
实习记者|曹年润
编辑|王珊
游戏成瘾
我关于网络游戏的调研其实持续了好些年。在2013年到2018年,我先后三次到四川芥县调研。四川省是中国西部的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芥县72.2%的人都是农业人口,近三成劳动力外出务工,外流人口不多,是一个典型的西部农业小县。这个地方足够具有“乡土基层社会”的代表性。
我的三轮调研都是关于中国偏远乡村社会各种复杂的教育事件如何促进了阶层或文化的再生产。社会学意义上的“再生产”强调一种关系的延续性与结构的稳定性。更通俗和现实一点来说,我的研究问题是这样的:乡村的学校和家长都在对学生们说,要好好学习,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如此来说,孩子们理当个个发奋图强。但事实是乡村学校一个初三年级能升上普通高中的都不太多,孩子们也很快认同这个现实。夹在矛盾中的他们生产出了一套反叛的文化,以让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获得反抗学校主流文化的安全感和成就感。我的关注点就是他们如何在有意识或无意识间,制造了这样一套走向再生产的意义符号和日常文化。

《狗十三》剧照
我第一次去调研是在2013年。我在芥县一所九年一贯制的云乡学校(化名)和学生们同吃同住了三个月。云乡学校位于芥县西南部的偏远山区,距离县城大约有40多分钟的车程。云乡是芥县唯一不通公交的乡镇。2006年后,芥县的村小全部撤并,学生大部分秉持“就近入学”的原则,到附近学校上学。上学距离变远,交通又不方便,寄宿成为乡村学校的主流。
刚到时,校长跟我讲,农村的孩子都挺淳朴的,乖得很,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在那里住得久了,我发现情况完全不是校长说的那样。云乡学校男生住一排平房,女生宿舍是一个三层小楼。学生们告诉我,晚上有女生会把床单系在一起,从三楼爬下去,和男生一起翻出校园,顺着校门口的河游泳。还有人翻出校园,走将近一小时的山路,到一个镇上上网吧。那时候智能手机已经比较普及了,学校禁止手机进校园,学生周末进校要检查,学生们就提前把手机放在校外的小卖部或其他地点,第二天出校倒垃圾的时候偷偷带进来,晚上在宿舍玩。
在这次调研里,我更关注的点其实是乡村学生的反叛与学校的空间、师生互动之间的关系。不过,网络游戏的沉迷在那时已经比较显露。
在班级里观察时,我发现孩子们聊天时经常讲到CF(穿越火线)等游戏,游戏的段位是他们相互炫耀的资本,他们用游戏来定义谁更牛,谁是老大。我一开始觉得是玩闹,但后来发现,网络游戏中的成功对他们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他们是真的希望在这套话语体系中成为成功者。

在课间十分钟,他们经常拿一张纸,围在一起一板一眼地复盘上周的战术,制定下周的计划。和我交流的时候,他们也会问,你玩什么游戏,几级了?他们希望借此了解和你是否有共同兴趣,能不能和你成为朋友,如果你懂他们的行话,而且游戏级别比他高,他们很快会对你产生崇拜。如果发现你不会玩某个经典游戏,他们就会觉得你很low。这些现象让我觉得他们基于网络游戏制造了跟学校主流的话语体系相对应的另外一套话语体系。
但在当时,因为有更加复杂的再生产研究需要去做,关于网络游戏对学生影响的观察和调研并没有深入进行。2018年11月,我到芥县开展第三轮调研,把“网络与游戏”作为一个子项目做系统的研究。从2013年到2018年,公众对孩子沉迷网络游戏这个现象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大家已经在讨论如何解决孩子沉迷网络的问题,很多研究是从管理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现象。
2018年,云乡学校已经被合并到隔壁镇一个规模大一点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对芥县24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的17所学校进行了调研,在这些学校的五年级和八年级分别随机抽取一个班级,对全体学生和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发放了2017份问卷,回收了1960份,同时对所抽班级的班主任、一些学生和家长展开了访谈。我们统计的数据显示,41.9%的农业户籍儿童日均玩手机或电脑一小时以上,上网从事娱乐类项目的占比达60.7%,我们把娱乐类项目分成“玩网络游戏”“网上聊天”“看小说和视频”等项目,玩网络游戏的比例最高,达到38.4%。

《老师·好》剧照
我们在问卷中用自感网络游戏成瘾度的主观指标和每天玩游戏多少小时等客观指标来综合评估学生玩网络游戏的成瘾度,在自感网络游戏成瘾程度这个问题上,我们设置了“瘾较小,适度玩”“瘾中等,能够控制自己”“瘾很大,时刻都想玩”三个级别,30.9%的农业户籍儿童自评玩网络游戏成瘾度在中等以上。由于我们是在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进行的调研,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并会在学生进校时进行检查,因此这个数据会低于假期的数据。班主任的评价和学生的自评非常不同,他们估算班上近八成学生网络游戏上瘾,三成成瘾严重,那些自评网络游戏成瘾较小的学生,在班主任眼里也经常是成瘾强烈的。
玩乐的缺失
2013年我在芥县开展第一轮调研的时候,孩子们还会组织一些传统游戏,比如山里闲逛,或者打牌。但之后几年去其他乡村调研,明显感觉以“熟人社会”为特征的乡土越来越像以“陌生人社会”为特征的城市社区了,很多时候大门紧闭,邻里间来往日益减少,乡村孩子们也和城市孩子们越来越像,都整天对着手机或电脑,宁愿给你发弹幕,也不愿意直接和你沟通。这和我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的体验有很大差别。

《小巷人家》剧照
我出生于四川绵阳下面的一个县城,上幼儿园之前跟着外婆在农村生活,读书后每年寒暑假也会去农村住一段时间。那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农村感受到的是无处不在的快乐和幸福。大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旁边就是亲戚,或者是关系很近的邻居。村里都是熟人,小孩不管跑到谁家里,总归沾点亲、带点故。不农忙时,大人会到村里的小卖部打牌,他们会带着小孩一起。游戏大多就是在集体纳凉聊天、相互串门走动的时候发生的,小孩跟小孩玩,去河里摸鱼、田里捉青蛙、地里“偷”西瓜。但现在的农村,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儿童也出去上学了,传统游戏发生的集体空间被解构了。
如何保障安全也成为问题。云乡学校属于雍村(化名),都是山地。村民以种植柑橘和茶叶为生,但收益并不好,2012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只有6856元。乡上只有一条稍宽点的路作为主街,路上只有一个产业——校门口的一个小饭店,还不是每天都有吃的。在这个乡的山村,大部分家庭都是隔代教育:爷爷奶奶帮外出打工的子女照顾孩子,最大的交代就是孩子不出事。
但说实话,孩子们去的地方有些我看了也觉得很危险。有一回他们带我去一个淘金洞,那个洞都快垮了;还有一回沿着山上流下来的小溪一路走,到一个离村子挺远的深水潭去抓鱼、游泳。他们就想找乐子、找刺激。村里的水塘、水库都年久失修,一到夏天,孩子们去游泳,掉下去都没人救。承担防溺水工作的乡村教师们,要沿着河道、池塘去巡逻。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长们反而认为网络游戏就像一个“机器保姆”一样,孩子在家游戏,安安静静地坐着,是听话的,安全的。

2018年我调研时看到,不上学时,孩子们基本在用手机在家里玩网络游戏,村里不是每家每户都有WiFi,有电脑和WiFi的孩子家里会成为小孩聚集地。一到饭点,家长们发现孩子跑没影了,也都知道去谁家找,一找一个准。
帮子女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们很难发现网络游戏的危险,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电脑、手机都不会用,没有网络游戏成瘾的概念,有的甚至以为孩子是在学电脑、上课。尤其是疫情之后,线上教学常态化,孩子总对着手机和电脑就更正常了。现在学生沉溺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教育部都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的办法。
寻找价值感
我在调研中发现,网络游戏对于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讲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早已超越娱乐与休闲的价值,甚至成为他们“自我救赎”的平台。
农村学校,也是以升学为中心。农村的家长只要有一线希望,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云乡学校是一所小微学校,九个年级共有171个学生,38个教师。为了提高孩子的成绩,和城里的学校一样,云乡学校对教室等空间的布局、课程表、各种考试的时间作了精确的安排,并设计了榜样激励等制度。你能感觉到学校在向学生传递一种思想:好好学习,遵守纪律,不要玩手机,通过中考、高考,考出去,改变命运。
最明显的设计是教室里的座次编排。云乡学校八年级只有一个班,总共19名学生,他们的座位被排成四列,中间两列是成绩优秀和表现良好的学生,边上两列是成绩不好和表现不佳的学生。座次每周轮换一次,仅限于纵向的轮换。根据教师的说法,这样编排是为了让中间两列的“好学生”和边上两列的“差学生”形成“一对一”的帮扶。

《同桌的你》剧照
然而,老师们的设想并未实现,这样的座次安排反而使学生内部分裂成了两个清晰的群体,并给“好学生”和“差学生”都带来了心理负担。被划分为“好学生”的一位女生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优越感,觉得自己优秀,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负担和心理压力,因为你需要努力学习才可以继续保持在中间的座次,否则成绩下滑后被放逐到两侧的座次上,是很没有‘面子’的。”
两侧的“差学生”则经历了“被歧视和被忽视”的感受,渐渐构建出一套自己定义成功的标准。网络游戏就是其中一个坐标。坐在两侧的一位男生带几分戏谑地对我说:“别看他们中间位置的‘好学生’在课堂上属于‘高大上’,我们两侧都是‘屌丝’,但一到打牌、喝酒、掏马蜂窝,特别是周末打CF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高大上’。让他们在周一到周五在教室里逆袭逆袭,也算是我们给他们机会了。”
“差学生”们还会用巧妙的话语捆绑“好学生”参与到他们塑造的价值体系中去,比如说,“你OUT了,连这么经典的游戏都没玩过,真是丢人啊!”“连游戏都玩不好,以后干啥事还能成功啊?”网络游戏就像社交货币一样在学生中间流通,不懂得网络游戏的人会遭到排斥。“好学生”终究是少数,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假意迎合,都是想融入这套话语的,因为不想被孤立。
他们本来在村里就已经很孤独了,很需要学校的社交价值。网络游戏无意识间建构起了一个行话共同体。被接纳的儿童拥有了属于“我们”的共同感,内部的团结与协作更加紧密。这套基于网络游戏的文化体系甚至能跟学校的主流文化相抗衡,因为学生们发现,学校传达的主流思想和现实并不一致——好好学习不一定能考上好高中——云乡学校的毕业生一大半都考不上普高,只能去职中。还有部分学生早早辍学打工。

《少年的你》剧照
我问过一些学生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回答我:做一个好厨师、当老板、做网红、做职业的游戏选手。在他们看来,网络游戏的“大哥”是切实的成功,“小弟”们很崇拜他,他们是有成就感、有价值的。可能越是在现实世界感觉到痛苦,越希望在虚拟世界感到成功。网络游戏可以解构他在现实世界中的无意义感、颓废感,他在现实中是“屌丝”,但在网络游戏里是超人。
权威的变更
网络游戏作为现代工业的一部分,底层逻辑是让玩家消费,相比于传统游戏对环境的挑剔,网络游戏便于参与,虚拟场景逼真,玩家可以任意选择并代入角色,产生真实的刺激体验。我发现,游戏背后的网络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在冲击学校和老师的权威。乡村里的孩子们首先发现,他们的老师不再是“知识权威”——乡村的教学日益依赖网络资源,而乡村教师普遍老龄化,往往搞不定网络难题。
我在云乡学校的学生口中听到的老师形象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只是同龄人中被淘汰的那批成绩最差的学生而已。他们收入很低,赚得还不如村里那些没读过书、在外打工的人多,知识陈旧,社会知识少,只懂得书本上那一套东西,在社会上根本没用。
这种“瞧不起”在行动上表现为扰乱课堂纪律。在一些学校的课堂上,专心上课的学生少之又少,一些学生直接制造干扰课堂的声音,不时以上厕所为由出去溜达一圈,甚至毫无理由地离座在教室内穿行。一节40分钟的课,老师可能有30分钟要花在维持纪律上。课堂之外,有些学生们也会拉帮结派地周期性犯错误,例如定期拿洗脚水泼宿舍门口的树。我问他们,下水道就在边上,为什么还泼树?他们说,就想把树浇死,表达对学校规则的愤怒。

《小欢喜》剧照
为了规范学生的行为,云乡学校在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分别位于教室走廊、男生宿舍平房区、女生宿舍楼道、校门口、学校办公区、操场口以及厕所外围,学校的每个角落几乎都处于监控之下。学校对此的官方解释是“为了保护师生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但校长会私下说,这是为了在全校学生中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学生不管你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不要违规。
但孩子的成长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的。摄像头的监控下,学生们的私密空间被极度压缩。在网络游戏里,学校的摄像头监控不到他们。网络游戏里也没有对时间的控制。在学校的安排下,学生们的童年被精确地划分为学习日、休息日。学生们早上6点起床,上午4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中午吃饭、上自习,下午也是4节课,如果是寄宿生,晚上还有2节自习课。学生们经常向我抱怨照课程表上一天课“像坐牢一样”。有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熄灯后偷偷打三国杀(一种纸牌游戏)、喝酒等等,因为“好不容易有个稍微长点的自由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早上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地做事,不自由了!”
学校里,孩子本应获得理解世界的知识、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和人格特质。但现在,学校注重普遍性的理论知识的传输和抽象思维的培养,忽视了“原创性探索精神”和“想象力”的培养,过早地抛弃了孩童与生俱来的“野气”和“自然气息”。你会发现,学生们知道北极,知道特朗普,知道复杂的几何公式,但不知道面前的植物是小麦还是韭菜。过去的课程里还有与家乡相关的、体验大自然的课程,以及春游、秋游,现在考虑到安全问题,很多出校的活动都被取消了。学校是一个围墙内的世界,和当地的社区是相互隔绝的。

《人世间》剧照
当然从学校的角度,这种忽视情有可原。乡村学校在经费和人员编制方面保运转尚且困难,更不要说投入更多资源去“精细化”和“个体化”地关爱每一个具体的留守儿童。总的来看,相较于城市儿童,乡村儿童在学校里、生活中都面临更多生活无意义感的境地,网络游戏逐渐成为他们逃离生活无意义感的唯一选择。如何根治乡村儿童网络游戏成瘾,背后的命题实际上是如何理解乡村儿童。

排版:初初 / 审核:小风
详细岗位要求点击跳转:《三联生活周刊》招撰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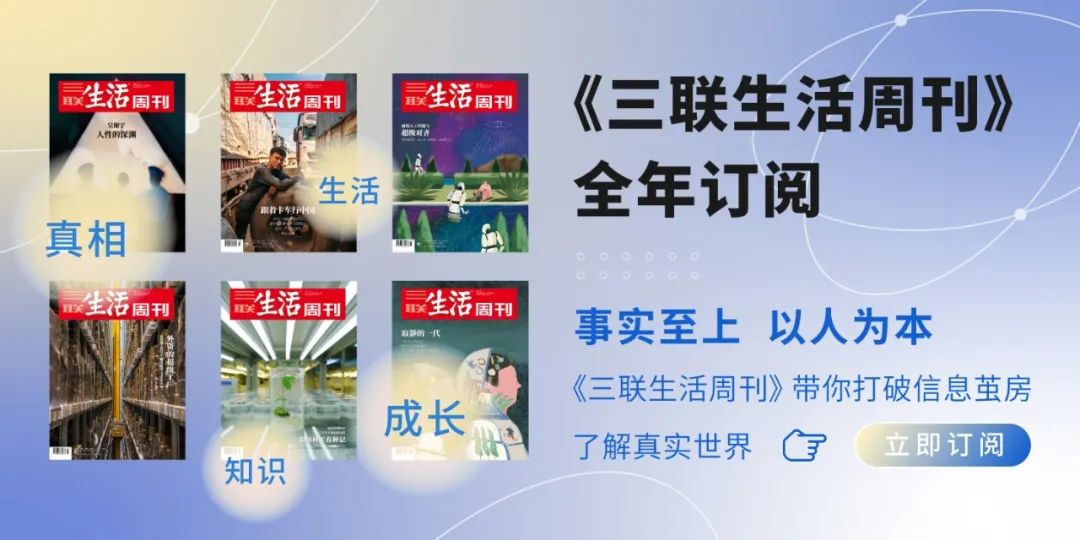
文章作者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发表文章525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5972人
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