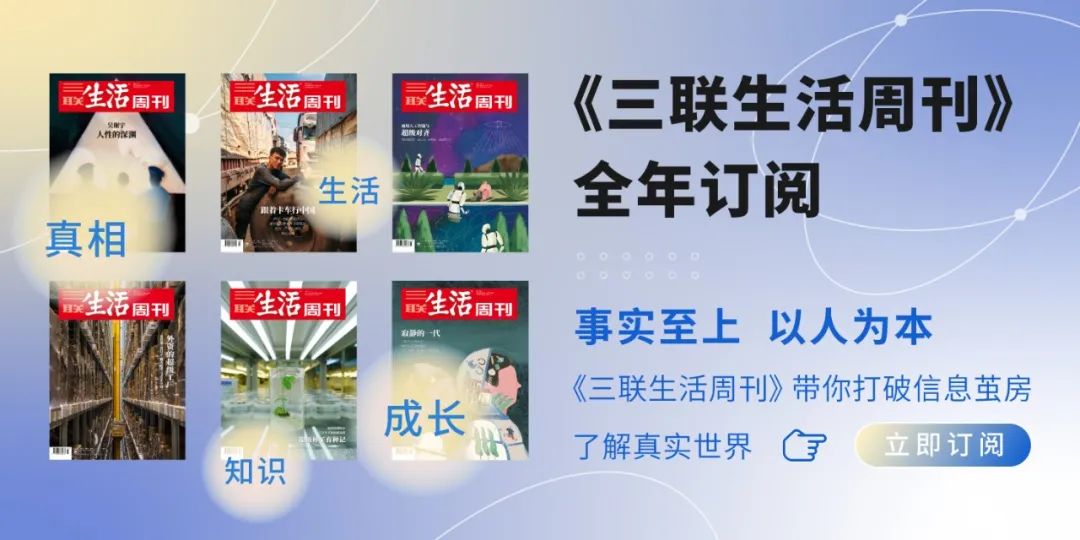*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儿子今年8岁半,身处“人嫌狗不爱”的阶段。但他丝毫不介意万物生灵“不待见”他,碰到任何人,他都能贴过去聊个五块钱的。
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在一起,他会和妹妹一起开餐厅,操着奶声奶气的腔调指挥妹妹团团转;和爸爸在一起,他会一脸严肃与老父亲讨论巴拿马运河事宜;和姥姥在一起,他不吝分享自己放又臭又大声的屁的心得;和同学在一起,他捡起地上的一根树枝,就能变身成战舰船长,和小伙伴们开始部署作战计划;和教他长笛的25岁的老师在一起,他们聊起对方两年前的婚礼,活像他就是现场的花童;和爸爸63岁的老板一起爬山,他俩走一路、聊一路,从以色列的节日到为什么中餐是世界无敌的,一个多小时的行程,全组年龄差最大的两个人,说的话比走的路都多。
《小舍得》剧照
我经常嫌他吵,但内心又真羡慕儿子源源不断的聊天欲和分享欲。他的语料库里,有星辰大海,不像我这个中年妇女,已经被磋磨成一个闷葫芦,不声不响地过完一天、又一天。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外向的人,年轻时和朋友、同事在一起,害怕冷场,总喜欢做那个不停说话和暖场的人;聊天时,一定不让话掉在地上,千方百计也要接下去、扶起来,让话题继续流动;我自己也喜欢和别人“掏心掏肺”,从童年往事、到刚出炉的八卦,从前男友的狗血、到婚后生活的鸡毛蒜皮,愿意分享给——不嫌我烦的——有缘人。
直到这两年,跟在洪流和岁月的身后亦步亦趋迈向中年的途中,我逐渐发现,那个曾经略聒噪的我,竟然开始玩起“沉默是金”。
我已经不记得像二十多岁时和好友彻夜长谈是什么时候了?即使在我三十岁出头时,我还具备在好友群里畅快聊天几小时的能力。那个时候,我碰到任何稀奇古怪、犹豫不决、难以入眠的事都想和他人分享,就像拿着满分试卷迫不及待要回家告诉父母的孩子。
几年前的有一天,我和伴侣吵架,生气出门散步消气,走到一家超市附近,越想越窝火。直接进到超市里面,连上WIFI,给好友打去视频,聊了好久。一开始是吐槽、后来话题就歪成手边货架上的几款唇膏,那个最好用。
和伴侣也是一样,恨不得把自己身边经历的一切都事无巨细分享给对方。我去路上买个咖啡,低头捡了一枚硬币,立即拨通对方电话,告诉他“今日份的幸运”;工作不顺,会隔着屏幕发过去几行叫苦叫累要辞职的狠言;如果周遭有八卦和秘辛曝出,更是要拉着伴侣晚上开“研讨会”,从故事的真实性、讨论到对我们婚姻和人生的启迪,全方位找角度,深挖、详谈,直到被尿憋到再也忍不住才不得不中断。
《小欢喜》剧照
年轻时的聊天欲,就像撒在地里的蒲公英种子,一到时节便肆意生长,被风一吹,落在哪里又能开出一片喧腾、热闹的新天地。而现在,作为资深中年人,聊天欲退化成了偏僻地区的手机信号,“喂喂喂”费劲半天聊两句就掉线。
我翻了翻与伴侣、亲朋好友之间的聊天记录,透着一股子“草木摇落露为霜”的萧瑟之气。
同伴侣之间的聊天已经全部化作功能性事务的沟通:“床单在打折,下单买了”“今晚儿子有游泳训练,记得早点去接女儿”“不做饭了,订个披萨”“9点有家长会,别忘了”。中年夫妻的聊天,就像跨部门合作的两个对接人在沟通:有事说事、没事勿扰。
至于和朋友聊天,会多带一些人的味道与温度,毕竟吐槽小孩和伴侣、控诉自己苦闷的中年生活是讲究情绪节奏和戏剧张力的,还做不到同聊天AI问询那样透着理智克己的风格。不过,终究是没有往昔淋漓尽致那股子劲儿了。别说线下攒个已婚已育中年女性聊天局有多困难了,就是拿着手机找对方聊天,现在也要思忖再三:她下班了还是在加班?辅导完孩子作业了么?是不是正在带孩子去辅导班的路上?我之前和伴侣因为这类事情吵过架,我现在问类似的问题会不会太敏感?
一场聊天局、几个当事人、八百个“心眼子”。最后,还是闭嘴,算了吧。
为什么中年人失去了分享欲、聊天欲——从曾经“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怡然自得、到如今发朋友圈自带的一份迟疑和倦怠?
年轻时,责任和负担较少,有大把时间陪朋友聊天、聚会、胡闹。但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后,生活节奏加快,责任也变重。白天被工作按头、晚上被娃纠磨,一整天下来,脑子只想静音、关机、清缓存。聊天变成了一种需要掂量的事。

《三十而已》剧照
虽然诸多研究表明,成年人之间高质量的友情能显著提升幸福感、缓解心理压力,但现实往往是,哪怕是最重要的友情,也常常被生活的洪流挤到一边。聊天邀约,最终输给了“孩子作业写完没”“洗碗谁做”“几点开家长会”这种中年人生FAQ。聊天的成本变得过高。
以前喜欢热闹、八卦、朋友圈里的一点点波澜也会让自己猎奇的DNA跳动。但现在,中年人就像老僧入定,这些凡尘俗事只会让自己感到疲惫。家里的亲戚找你说事情、朋友找你诉说、同事找你吐槽,你知道大多时候都是新瓶装老酒,翻不出个新花样。无非是长辈身体不好住院了、养生被骗了、婆媳不和了;朋友的熊孩子又作妖了、老公依旧不靠谱、自己快要失业了;而同事,骂领导、骂甲方,说了几百遍的“要辞职”,最后还是乖乖去加班做PPT了。
中年人的情绪如储水池,得先给工作、家庭、娃的辅导作业腾出空间,哪里还塞得下别人的emo和drama?除非是真正要好的朋友,她发过来的那句“最近有点烦”你还想接,其他的淡如水之交,点个赞就当当回应、祈祷、祝福了。当一个中年人,不再有精力处理别人的情绪风暴或复杂人际时,自然会选择远离那些总是带来纷扰的朋友。不是我们变冷漠了,只是自我保护机制加强了。
而且,成熟的中年人,深谙“沉默是金、闭嘴显贵”的道理。
前些日子,亲戚群里掀起了一场催婚表妹的运动。表妹年过三十、和男友恋爱三年多,俩人至今没有结婚的打算。小年轻不急、爹妈长辈很上火,尤其是女方家庭。女儿这个年纪、有恋人不结婚、不生娃,比单身的更让世俗难容。于是,群里不知道谁起的头,长辈们开始轮番上阵游说。
《欢乐颂》剧照
众说周知,长辈开口,先上价值、再讲道理、最后给你出一张感情牌,一通操作下来,满屏的小作文、外加几十条60秒的语音。而以表妹一方为代表的几个小辈,虽然势单力薄,但也凭借着年轻气盛、能舌战群儒。只有群里的中年人,集体噤声。我不知道那些中年人沉默的理由是否和我一样:这个事哪有标准答案和正确答案?这个事长辈管得了?这个事小辈躲得掉家长的批判?这个事——和我有啥关系!
既懂得长辈的焦虑、又理解小辈的选择、还事不关己,那我们中年人就当自己是进了曹营的徐庶,要有一言不发的觉悟。
总之,中年人与他人聊天的欲望,就像对饮,大多时候失去了当年大口吹瓶、豪情万丈的兴致——除非,你能够遇到对胃口的人。能让我消退的“聊天欲”从“沉默模式”切换到“畅聊频道”的人目前只有一类:就是确实能给自己带来新知见闻的人,我称之为“知识型交流”。
当有人抛出一段有营养的内容时,脑海中会迸发出“啊哈!”时刻,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真的假的?!”会有一种轻微触电的小兴奋,这是大脑分泌出的多巴胺在奖励我们。
去年,我结识了一位略小我几岁的钢琴演奏家。她学古典乐科班出身、多年学琴背景、也有登台表演的经历。我们曾因为孩子一起学棋相识,最后俩孩子中途放弃学棋,但我们因为性格合拍、能聊到一起成为了新友。每周,我们会定期约吃中饭、或者喝杯咖啡,她和我讲讲古典乐的历史、钢琴的类别、音乐家的八卦,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就像生活打开了一扇新天窗。
更重要的是,这类吸收新知的交谈会让中年人觉得自己“还在线”。
看多了“30岁看不懂年轻人的梗”“35岁被职场淘汰”“40岁难就业”“人到中年只想摆烂和躺平”这样的新闻,自己难免会有一种日暮西山、走向迟暮的心慌感——怎么刚送走青春就迎来老年了?还在爬坡的路上、未登峰造极,就要被踢走滚下坡了?
《都挺好》剧照
James Hollis在《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成型》一书中写道: “中年,是一段从痛苦到意义的旅程。生活召唤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解决年轻时的狂妄和膨胀,并教导我们区分希望、知识和智慧。希望通常基于可能发生的事情;知识是有价值的经验之谈;而智慧总是使人谦卑,永不膨胀。” 因此,中年人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求——非职业性和功能性——可能比年轻时更渴望。此时,吸收新知能给我们带来一种内心的安慰:我还没有向这个时代和自己的人生缴械投降。
当然,我还期待另一类让我有聊天欲望的人:是那些让我在情绪上可以毫无伪装、率真做自己的聊天伙伴。
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倾诉者,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聊天,就像打开窗户通风,自由舒畅。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情绪和见解,无论是喜悦还是委屈,都能够被理解与接纳。这样的沟通无需刻意克制、隐藏真实感受,也不用担心脱口而出的言语是否会令自己陷入难堪或不自在。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能万年才能修得这么一位让彼此心意相通、又毫无负担的友人吧。
在我心中,这种关系的典范,是比尔·盖茨与他在湖滨中学时结识、后因登山遇难的挚友肯特·埃文斯;是《老友记》里的“蠢萌”的乔伊和“无厘头”的钱德勒,虽然看似不靠谱,却始终是彼此最安全的情绪出口;也是《挪威的森林》里的渡边与永泽,二人在迷茫与孤独中,用深夜宿舍里的闲聊支撑着彼此走过一段难熬的人生阶段。
《老友记》剧照
只是,上述这些典范要么是学生时代的默契,要么是人生初段的热血结识,似乎与中年无缘。可中年,它兵荒马乱、风雨交加、让人心生无力,恰是一段需要倾诉和共鸣的时期。如果在这场兵荒马乱中,我们能找到令自己轻盈的聊天伙伴,人生何其幸啊!
排版:初初 / 审核:雅婷
本文为原创内容,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文末分享、点赞、在看三连!未经许可,严禁复制、转载、篡改或再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