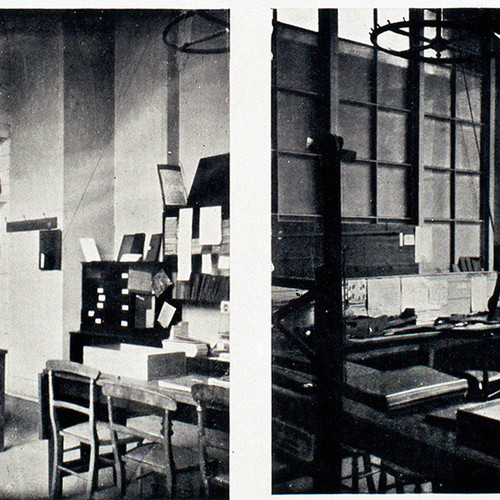一项持续53年的研究:成为天才需要什么?
作者:陈璐
09-03·阅读时长18分钟

12岁的乔·贝茨(Joseph Bates)因为成绩遥遥领先于其他同龄人,在父母的安排下参加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暑期计算机科学项目。这个年纪的孩子,按理说应该还在为普通的学校作业发愁,但贝茨却在大学的课堂上游刃有余。他不仅轻松地掌握了课程内容,还忙于教比他年长的研究生如何编写FORTRAN代码。
这是1968年的故事。这种情况引起了讲师多丽丝·利特克(Doris Lidtke)的注意,她给教授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Stanley)打了电话。斯坦利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以研究心理测量学(认知能力研究)而闻名。他为贝茨安排了一系列测试,包括通常由16~18岁的准大学生参加的SAT考试。
贝茨的成绩非常高。斯坦利于是尝试为贝茨寻找一所愿意接纳他学习高级数学和科学课程的高中,但没有学校愿意破例。最终,斯坦利说服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前院长卡尔·斯旺森(Carl Swanson),让13岁的贝茨以本科生身份入学,学习物理和计算机科学。在大学期间,贝茨表现依旧出色。17岁时,他已经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的硕士学位,并在1979年于康奈尔大学完成了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业。如今,贝茨是一名专注于人工智能娱乐领域的科学家。
斯坦利亲切地称贝茨为他的“零号学生”,因为他很快发现自己对发掘和培养那些智力早熟的青少年产生了深深的兴趣。1971年,他从斯宾塞基金会得到了266100美元,启动了一个为期五年的项目,旨在寻找并帮助那些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表现出非凡天赋的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他想让这些孩子能够尽早接触到适合他们的高级课程,最大限度地开发他们的潜力。这个项目后来被称为“数学早熟青少年研究”(Study of Mathematically Precocious Youth,SMPY)。

与此同时,斯坦利的工作还促成了197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天才青少年发展中心(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cademically Talented Youth,CTY)的成立。这个中心的目标很简单:寻找世界各地具有天赋的青少年,把他们带到大学校园,让他们能够学习那些超出他们年龄的高级课程。这个项目培育了许多如今家喻户晓的名字——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Google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流行音乐巨星Lady Gaga,以及在电影《哈利·波特》中扮演卢娜·洛夫古德的伊文娜·林奇也是其中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CTY如今也为2~6年级的儿童提供暑期项目。
斯坦利在53岁开始这项研究时,因为临近退休,最初只打算进行一个为期五年的研究计划。但他的学生卡米拉·本博(Camilla P. Benbow)在1976年加入后,希望能够追踪这些学生的一生。她建议增加组群,将对兴趣、偏好、职业和其他生活成就的评估纳入进来,深入了解他们的发展轨迹。斯坦利听后鼓励了她的选择。于是卡米拉成为SMPY的负责人,并最终将其发展为了一个跨度半个世纪的纵向研究。
1990年,大卫·鲁宾斯基(David Lubinski)也加入了进来。1998年,他们两人将项目从爱荷华州立大学迁至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因为卡米拉成为范德堡大学皮博迪学院(Vanderbilt Peabody College )的院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斯坦利的研究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他当初正是在皮博迪学院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
“我们在研究中增加了两个新群体,”大卫·鲁宾斯基教授在视频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一个群体是在爱荷华州确定的第四批学生,另一个是在1992年被识别为顶尖STEM研究生的群体。我们在他们33岁和50岁时对他们进行了追踪研究。”
在过去53年时间里,这个项目跟踪了5000多名在全美被认为最聪明的那1%的孩子,对他们的特殊才能进行了一项史无前例的长期研究。这些孩子在七年级时已经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定量、语言和空间推理能力。研究表明,这些在年轻时就展现出天赋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成为各自领域中的高成就者。尤其是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那些在数学和科学能力方面表现优异的孩子,往往在成人后脱颖而出;而那些在语言能力方面表现突出的孩子,则更有可能在人文学科和法律领域中取得成就。
“你看那些进入前1%成绩线的参与者,其中有25%的人拥有博士学位;而在前0.01%的参与者中,这个比例上升到了50%。但这只是结果的一部分。我们还研究了他们的收入、发表的文章以及其他各种积极的成果,因为表达天赋的方式有很多种。不论怎样,能力越强越好,虽然其他因素也很重要,但数学、语言和空间推理等能力仍然是关键。”大卫·鲁宾斯基教授在采访中如是说。
尽管SMPY研究的参与者是匿名的,但有不少人成年后选择公开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个项目。比如31岁便获得菲尔茨奖的数学家陶哲轩、神经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林·卡麦勒,以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苏珊·阿塞,她在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中获得了最佳经济学家奖。可以说,不论是CTY还是SMPY,这些项目发现和培养的天才人物,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

如今,寻找极具天赋的年轻人才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每年,华为公司高薪招聘“天才少年”的新闻总能引发公众的关注。然而,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和教育体系对人才的培养并不总是同步的。在教育政策中,天才儿童往往被忽视。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孩子不需要特别的关注,但SMPY的研究表明,那些通过跳级来学习与其能力相匹配课程的孩子,比按部就班接受传统教育的同龄人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大成就。
所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追踪研究,我们是否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智力早熟青少年的独特需求?是什么决定了他们一生中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康奈利厄斯·范德堡心理学教授、数学早熟青少年研究(SMPY)的联合主任大卫·鲁宾斯基。

智商的差异仍然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大多数时候,当我们想到天才时,总是想到高智商人群。但相比于我们通常认为用以衡量天才的“智商”测试,SMPY主要利用SAT考试来识别天才儿童。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SAT会成为你们的主要筛选工具?
大卫·鲁宾斯基:当天才搜索刚开始时,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通过他著名的“天才的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1921)——这可能是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纵向研究——研究了1500多名智商排名在前1%的青少年。当时他们只能使用智商测试进行单独评估,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测量方法。然而,特曼很早就意识到除了智商这种普遍能力之外,还有一些特定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轨迹为学生量身定制教育方向。遗憾的是,当时他并没有合适的测量工具。同时特曼还强调了早期兴趣的重要性,因为单靠能力无法揭示一个人真正的兴趣所在。
当斯坦利开始SMPY项目时,他知道特曼的测试错过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即半导体的发明者之一威廉·肖克利以及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他们都参加了特曼的智商测试,但没能达到前1%的标准。如果当时测量的是数学推理或空间能力,他们就会被识别出来。
斯坦利之所以选择SAT,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测试,能够精确测量定量推理和语言推理能力。SAT的设计初衷是为筛选准备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因此它拥有大量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数据。斯坦利将这项测试来评估那些在学校标准化成绩测试中排名前3%的孩子,发现这些在7年级时排名前3%的学生,在SAT得分上的分布与年长五岁、为上大学做准备的高中生相同。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那些在12岁时得分能够达到高中毕业班学生平均水平的孩子,可以在三周内完成一整年的高中课程。而那些得分在前5%的孩子,也可以同时完成两门这样的课程。并且他们都非常享受这种学习方式。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这是否说明智商与天才或者成就并不那么紧密相关?
大卫·鲁宾斯基:天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定义天才的方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我们指的是那些真正改变了文化的人物,比如史蒂夫·乔布斯、爱因斯坦、牛顿,或者莎士比亚等。在我们研究的学生中,他们展现出了在学习、存储和处理复杂抽象学术材料方面的非凡潜力。有些人称他们为“符号分析师”,因为他们极为擅长分析、存储和处理定量/数值、语言/文字以及空间/图像符号,而这三种能力是互相关联的。
实际上,人们往往低估了特曼所使用的一个标准——智力排名前1%的学生。许多人将这个标准视为单一的类别,但事实上,即便是在这前1%的学生中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今,我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智商测试,转而关注更具体的能力和其他相关因素。智商排名前1%的分数线大约为137,但智商实际上可以高达200以上。数学、空间和语言能力也是如此:前1%涵盖了能力范围的三分之一。这种差异极其重要。天才、超常天才、极端天才之间的差别,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微妙,但在他们的成就和影响力上却有着显著的体现。在我们研究的这些排名前1%的学生中,处于前25%和后25%的学生在创造性成就和职业地位上的差距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卓越的智力天赋其实是一个光谱
三联生活周刊:SMPY强调了定量推理(mathematical ability)、语言推理(verbal reasoning)和空间能力(spatial ability)这三种能力对于识别天才儿童的作用,其中你提到空间能力往往被低估了。
大卫·鲁宾斯基:是的,这种能力常常被忽视。现代的天才搜索程序在识别前1%优秀儿童时,往往会错过那些在空间能力上特别出众的孩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在STEM领域,建筑、创意艺术、骨科手术和牙科等领域,空间能力的天赋是极为重要的。而那些在空间能力上特别有天赋,但在语言或定量能力上稍逊一筹的孩子,正是我们社会基础设施中不可或缺的高级技工、木匠、电工和管道工所需要的人才。军事系统在选拔时对空间能力的重视做得相当出色,他们至今仍然使用这种能力的测试。然而在学术领域,这种能力却常常被忽略了。
三联生活周刊:人文学科与STEM领域的天才儿童,是否也存在不同能力的区别?
大卫·鲁宾斯基:人文学科的学生在智力结构上更偏重于口头表达。尽管这些孩子的数学和语言推理能力也都处于前1%的水平,但他们在青年时期所展现的不同智力模式预示着他们未来在教育、职业和创造性成果上的不同发展路径。
卓越的智力天赋其实是一个光谱,没有明确的分类线。无论是空间能力、定量推理能力还是语言推理能力,这些能力之间的组合可能性千差万别。有些学生在数学上表现出色,但在其他方面与普通人无异;也有些学生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优异。
理解能力的水平和模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往往决定了未来的发展路径。不同的能力优势将他们引向截然不同的终点——参与者往往会在那些最能发挥他们潜力的领域中发展自己的才能。能力模式的差异,如同兴趣的差异一样,指引着人们走上各自独特的发展道路。而能力水平的高低,加上坚定的决心,最终决定了当机会降临时,他们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值得注意的成就。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发现对我们看待天赋的培养有何影响?
大卫·鲁宾斯基:基本上,我们谈论的是“适当的发展安置”。每个孩子都有权利每天学到新的东西。在美国,如果你看看那些年龄在17岁及以下的12年级学生,会发现其中有15%的人在一般知识方面比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知道得更多。这种知识储备上的个体差异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孩子们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接受远程指导。这种巨大的差异无疑令人兴奋,但也带来了挑战。当面对课堂上如此悬殊的个体差异时,比如有些孩子在九年级时就已经掌握了高中所有的数学知识,我们该如何应对?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同意如今发达的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个人发展他们独特的天赋?这些技术进步也会影响天才儿童的鉴定或测试标准吗?
大卫·鲁宾斯基:每一种强大的工具都有其两面性。自从人类发现火和工具以来,我们便知道它们既可以用来造福,也可以用来伤害。我们非常关心青少年在互联网上消费的内容,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潜在的积极一面,互联网为学生提供了以他们喜欢的快速学习高级学科的机会。在人才识别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程序,至于人工智能的介入,它的潜力和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导致个体差异的,往往是家庭之外的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英国有部纪录片叫《人生七年》(7 Up),同样也在跨度半个多世纪里追踪记录了14位英国的7岁儿童的生活。在那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家庭背景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在SMPY中,你是否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如果家庭环境对人才培养的影响是如此显著,我们如何帮助那些来自不利家庭背景的孩子?
大卫·鲁宾斯基:那项研究的样本量非常小,而要得出具有科学意义的结论必须依赖大样本的研究。事实上,有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行为遗传学研究。当然,家庭环境很重要,但真正导致个体差异的往往是家庭之外的环境。家庭内部的环境并不会直接导致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例如,那些从未见过亲生父母却在健康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被收养的孩子,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们的能力、兴趣或性格往往与养育他们的父母没有太多相关性,反而与从未见过的生物学父母相关性更高。所以,必须通过大规模的样本研究才能看清这一点。我建议参考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的《行为遗传学》(Handbook of Behavior Genetics),这本书经过多次修订,他在书中详细探讨了这些问题,包括许多大规模的双胞胎和收养婴孩研究。这些在技术上被称为生物计量学知情研究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家庭之外的环境具体是指什么?
大卫·鲁宾斯基: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他们会越来越多地选择或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他们选择课程、朋友、运动、乐器,决定何时学习、何时聚会等等。这些选择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显著增大,这就是我所说的家庭之外的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有这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在研究中我们该如何选取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呢?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了你对天才的理解?
大卫·鲁宾斯基:人们往往倾向于寻找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人类并不简单。要理解一个人,首先需要全面评估他们的个性化特质,因为在认知能力的水平和模式上,人们存在显著差异。他们的兴趣、性格、机会也各不相同。
天才(genius)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我们研究的方向是识别出具有非凡智力能力的人,这些能力可以分为三种:定量推理、语言推理和空间能力。这些能力在科学、人文学科、创意艺术等领域都至关重要。但能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还要考虑兴趣。你对哪些学科充满热情?创意艺术、科学、数学、建筑等领域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找到你的热情所在。此外,性格也很重要。即使两个人的能力和兴趣相似,但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他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路径也会大不相同。
因此,要真正理解一个人,我们需要将这些所有因素纳入考虑。在我工作的大学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高成就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这样的生活。有些人觉得每周工作30小时足矣,因为他们想把时间花在其他事上。再比如,有人因为家庭责任无法搬离社区,有人则毫无束缚;有人渴望孩子,有人则无此意愿;有人热爱旅行,有人却更喜欢安定。这些差异都影响着他们的选择与生活轨迹。正是这种个体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教育、职场和创造力方面的发展。这其中没有对错之分,目标是基于你的个性为自己创造和/或选择正确的道路。人们可以寻求建议,但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我注意到,你们在中后期的职业追踪调查中会询问诸如“你对自己的职业是否满意”“是否觉得自己过上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问题。这些资优生对“有意义生活”的不同定义,似乎确实影响了他们未来的发展。
大卫·鲁宾斯基:人们对成功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认为成功意味着每周工作40小时就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可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朋友,做志愿者,或者去旅行。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是成功。而另一些高成就者则会觉得每周工作40小时太少了,因为他们热爱工作,热爱自己的专业,渴望推动知识的前沿发展。这让他们感到生活有意义。创造一个令人满意、充实、有意义的生活有很多种方式,而我们从中学到的是,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兴趣和性格。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调整。最初,当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是青少年时,重点在于寻找最优的教育干预措施。随着他们成长为成年人,我们的关注点转向了职场行为,探索是什么因素导致他们在工作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成就感和满足感。接着,我们开始研究创造力和卓越,试图理解是什么使一个人在医学、法律等领域成为出色的专业人士,或者推动知识的前沿发展。现在,我们还研究他们的志愿者工作,探索是什么让他们的生活充满意义,以及他们如何规划退休生活、如何分配时间,家庭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我们问及他们最为自豪的事情、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时,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他们提到家庭的频率是提到职业的两倍。
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来自不同世代的孩子在教育和职业选择上有不同吗?像特曼就曾提到,天才的诞生与时代支持的能力有关,过去对古典音乐的推崇造就了贝多芬和莫扎特,而今天的社会可能更有利于科技天才的发展。
大卫·鲁宾斯基:绝对如此。比如,女性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机会。而如今,在美国的过去15年里,女性获得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都超过了男性。这在特曼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这种机会的增加是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因此,我们不应该只看人口统计数据,而应该关注个人,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尽管这很难做到,但这是我们的目标。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趋势是否反映了社会或教育系统的某些变化?
大卫·鲁宾斯基:我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更加灵活。以阅读水平为例,在美国,10%的9岁儿童,其阅读水平已经超过了17岁青少年中表现最差的25%。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同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教育需求,需要不同的机会。这在数学能力和空间能力方面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学生的个性化特质,然后根据他们的需求量身定制教育课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差异表现,我注意到你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STEM领域,女性较少的原因更多是由于职业选择而不是能力差距。在这项研究中,你们还有其他关于性别差异的惊人发现吗?
大卫·鲁宾斯基:我们已经观察到这些差异几十年了。随着机会的增加,女性更倾向于选择有机材料(organic material,指涉及与人或生命系统打交道的健康科学、教育和公共管理等领域),而男性则更倾向于无机材料(inorganic material,指专注于非生命系统、涉及处理抽象概念、物理材料或技术的学科)。当然,这两个选择的分布是高度重叠的。例如,我们那些在数学上有天赋的女性确实会进入STEM领域,但她们更有可能选择医学和法律,而男性则更可能进入工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当你观察这些女性的职业选择时,那些进入法律领域的数学天才女性通常从事的是知识产权法、环境法、专利法等专业。我们曾在文章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如果一位在数学上有天赋的女性用她的专业知识在环境法领域保护了阿拉斯加的一片土地免遭开发,那谁能说这不是对人类更大的贡献呢?相比之下,同样聪明的男性可能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物理宇宙的文章。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SMPY项目中的第五批参与者与前四批不同,他们是1992年就读于美国顶尖数学/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而非“天才儿童”。实际上,在天才研究的历史中,通常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识别天才儿童,另一种是识别天才成人。在这个项目中,你们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到目前为止,这组研究对象展现了哪些与前四组不同的发现?这些发现对项目提供了哪些新的启发?
大卫·鲁宾斯基:1992年,我们识别了714名参与者,他们是当时美国顶尖STEM项目中的研究生,来自加州理工、麻省理工、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顿等顶尖学校。我们在他们33岁和50岁时分别进行了跟踪研究。虽然我们可以将他们与前四组进行比较,但更有意义的是与他们的同行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这些顶尖项目的研究生与职场中的其他同龄人区别明显:他们通常有更强的能力,更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并且工作更努力。很多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前1%的人群中,能力差异也很大,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这两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来验证天才的识别。识别12岁孩子的能力是最有说服力的。如果你通过一个两小时的测试就能预测一个孩子未来获得博士学位的可能性为50%,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结果——毕竟在美国,只有大约2%的人能够获得博士学位。但通过第五组的研究,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测量空间能力,效果会更好。我们在几百名12岁的学生中测量了他们的空间能力,但我们并没有一开始就选择他们。如果我重新进行这项研究,最有潜力未被开发的智力来源于空间能力。我们2021年发表了文章《过去50年我们学到了什么?》,在文章结尾部分提到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首要重点就是建立一个人才搜索机制,以识别并培养在空间能力方面有天赋的儿童。
三联生活周刊:未来SMPY项目将会继续解决哪些尚未解答的问题?
大卫·鲁宾斯基:我们正在筹备首次针对65岁年龄段研究对象的跟踪调查,计划于2027年1月启动。这次研究将重点关注他们上次50岁时接受调查谈到的成就感与遗憾。退休后,他们将如何分配时间?会不会参与志愿者工作?会不会传授自己的智慧?会不会与儿女和孙辈们共度时光?在支持孩子学习需求方面,他们遇到了哪些挑战?这些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变化?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又如何促进这种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将要探讨的重点。
文章作者


陈璐
发表文章77篇 获得0个推荐 粉丝258人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现在下载APP,注册有红包哦!
三联生活周刊官方APP,你想看的都在这里